楚词的历史地位及历史意义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神马作文网作业帮 分类:语文作业 时间:2024/11/14 00:52:38
楚词的历史地位及历史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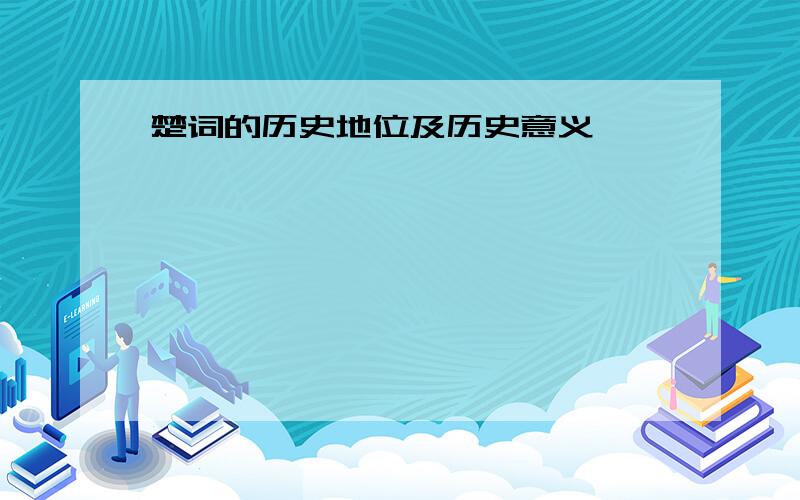
楚辞:
楚辞是一种在战国时代由楚国的诗人吸收南方民歌的精华,融合上古神话传说,创造出的一种新体诗.楚辞打破了《诗经》四字一句的死板格式,是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一次大的解放.楚辞采取三言至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篇幅和容量可根据需要而任意扩充.形式上的活泼多样使楚辞更适宜于抒写复杂的社会生活和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楚辞的代表作家有:屈原.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如前所述,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现存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还有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舟子的唱辞: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汉人又有“赋者,古诗之流也”一说(见班固《两都赋序》),当是为了攀附儒家经典,兼考虑到赋的铺张特征.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见《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离骚》这篇代表作的构架,由“卜名”、“陈辞”、“先戒”、“神游”,到“问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前所述,春秋以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这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他们“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
当然,“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
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楚辞是一种在战国时代由楚国的诗人吸收南方民歌的精华,融合上古神话传说,创造出的一种新体诗.楚辞打破了《诗经》四字一句的死板格式,是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一次大的解放.楚辞采取三言至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篇幅和容量可根据需要而任意扩充.形式上的活泼多样使楚辞更适宜于抒写复杂的社会生活和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楚辞的代表作家有:屈原.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如前所述,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现存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还有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舟子的唱辞: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汉人又有“赋者,古诗之流也”一说(见班固《两都赋序》),当是为了攀附儒家经典,兼考虑到赋的铺张特征.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见《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离骚》这篇代表作的构架,由“卜名”、“陈辞”、“先戒”、“神游”,到“问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前所述,春秋以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这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他们“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
当然,“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
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