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索亚历险记主要内容有没有50至100字的?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神马作文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11/11 17:06:13
汤姆索亚历险记主要内容有没有50至100字的?
不仅要简洁,还要能概括全课文【是语文书上第17课的】
不仅要简洁,还要能概括全课文【是语文书上第17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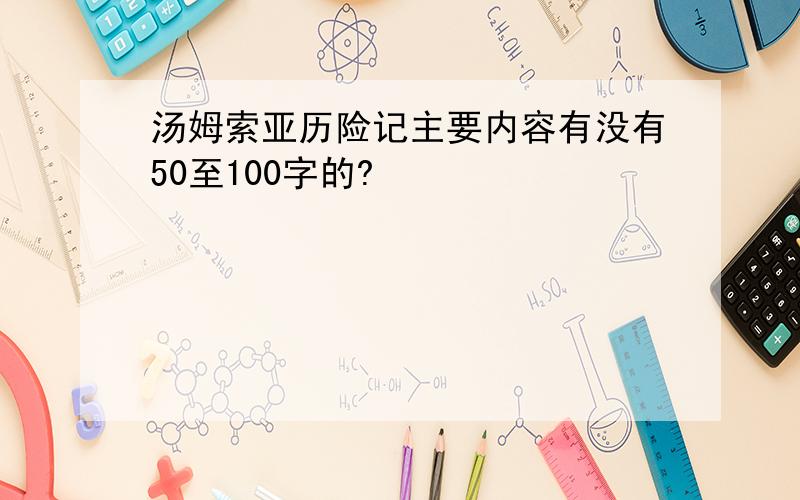
星期六的早晨到了,夏天的世界,阳光明媚,空气新鲜,充满了生机.每个人的心中都荡漾着一首歌,有些年轻人情不自禁地唱出了这首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欢乐,每个人的步都是那么轻盈.洋槐树正开着花,空气里弥漫着芬芳的花香.村庄外面高高的卡第夫山上覆盖着绿色的植被,这山离村子不远不近,就像一块“乐土”,宁静安详,充满梦幻,令人向往.
汤姆出现在人行道上,一只手拎着一桶灰浆,另一只手拿着一把长柄刷子.他环顾栅栏,所有的快乐,立刻烟消云散,心中充满了惆怅.栅栏可是三十码长,九英尺高啊.生活对他来说太乏味空洞了,活着仅是一种负担.他叹了一口气,用刷子蘸上灰浆,沿着最顶上一层木板刷起来.接着又刷了一下,二下.看看刚刷过的不起眼的那块,再和那远不着边际的栅栏相比,汤姆灰心丧气地在一块木箱子上坐下来.这时,吉姆手里提着一个锡皮桶,嘴中唱着“布法罗的女娃们”蹦蹦跳跳地从大门口跑出来.在汤姆眼中,到镇上从抽水机里拎水,一向件令人厌烦的差事,现在他可不这样看了.他记得在那里有很多伴儿.有白人孩
子,黑人孩子,还有混血孩子,男男女女都在那排队等着提水.大家在那儿休息,交换各自玩的东西,吵吵闹闹,争斗嬉戏.而且他还记得尽管他们家离拎水处只有一百五十码左右,可是吉姆从没有在一个小时里拎回一桶水来——有时甚至还得别人去催才行.汤姆说:
“喂,吉姆,如果你来刷点墙,我就去提水.”
吉姆摇摇头,说:
“不行,汤姆少爷.老太太,她叫我去提水,不准在路上停下来和人家玩.她说她猜到汤姆少爷你会让我刷墙,所以她吩咐我只管干自己的活,莫管他人闲事——她说她要亲自来看看你刷墙.”
“咳,吉姆,你别管她对你说的那一套.她总是这样说的.
把水桶给我——我很快就回来.她不会知道的.”
“哦,不,我可不敢,汤姆少爷.老太太她会把我的头给拧下来的,她真的会的!”
“她吗?她从来没揍过任何人——她不过是用顶针在头上敲敲罢了——谁还在乎这个,我倒是想问问你.她不过是嘴上说得凶,可是说说又伤害不了你——只要她不大叫大嚷就没事.吉姆,我给你一个好玩意,给你一个白石头子儿!”
吉姆开始动摇了.
“白石头子,吉姆!这可是真正好玩的石头子啊.”
“嘿,老实说,那是个挺不错的好玩意.可是汤姆少爷,我害怕老太太……”
“还有,吉姆,只要你答应了的话,我还给你看我那只脚趾头,那只肿痛的脚趾头.”
吉姆到底是个凡人,不是神仙——这诱惑对他太大了.他放下水桶,接过白石头子儿,还饶有兴趣地弯着腰看汤姆解开缠在脚上的布带子,看那只肿痛的脚趾.可是,一会儿之后,吉姆的屁股直痛,拎着水桶飞快地沿着街道跑掉了;汤姆继续用劲地刷墙,因为波莉姨
妈此时从田地干活回来了.她手里提着一只拖鞋,眼里流露出满意的神色.
不过,汤姆这股劲没持续多久.他开始想起原先为这个休息日所作的一些玩耍的安排,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再过一会儿,那些自由自在的孩子们就会蹦跳着跑过来,做各种各样
开心好玩的游戏,他们看到他不得不刷墙干活,会大肆嘲笑挖苦他的——一想到这,汤姆心里就像火烧似的难受.他拿出他全部的家当宝贝,仔细地看了一阵——有残缺不全的玩具、一些石头子、还有一些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这些玩意足够用来换取别的孩子为自己干活,不过,要想换来半个小时的绝对自由,也许还差得远呢.于是他又把这几件可怜的宝贝玩意
装进口袋,打消了用这些来收买那些男孩子的念头.正在这灰心绝望的时刻,他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这主意实在是聪明绝伦,妙不可言.
他拿起刷子,一声不响地干了起来.不一会儿,本·罗杰斯出现了——在所有的孩子们当中,正是这个男孩叫汤姆最害怕.汤姆最怕他的讥讽.本走路好像是做三级跳——这证明他此时的心情轻松愉快,而且还打算干点痛快高兴的事.他正在吃苹果,不时地发出长长的、好听的“呜——”的叫声,隔会儿还“叮当当、叮当当”地学铃声响,他这是在扮演一
只蒸汽轮船.他越来越近,于是他减慢速度,走到街中心,身体倾向右舷,吃力、做作地转了船头使船逆风停下——他在扮演“大密苏里号”,好像已吃水九英尺深.他既当船,又当船长还要当轮机铃.因此他就想象着自己站在轮船的顶层甲板上发着命令,同时还执行着这
些命令.
“停船,伙计!叮——啊铃!”船几乎停稳了,然后他又慢慢地向人行道靠过来.
“调转船头!叮——啊铃——铃!”他两臂伸直,用力往两边垂着.
“右舷后退,叮——啊铃——铃!嚓呜——嚓——嚓呜!嚓呜!”
他一边喊着,一边用手比划着画个大圈——这代表着一个四十英尺大转轮.
“左舷后退!叮——啊铃——铃!嚓呜——嚓——嚓呜——嚓呜!”左手开始画圈.“右舷停!叮——啊铃——铃!左舷停!右舷前进!停!外面慢慢转过来!叮——啊铃——铃!嚓——呜——呜!把船头的绳索拿过来!快点!喂——再把船边的绳索递过来——在发什么呆!把绳头靠船桩绕住好,就这么拉紧——放手吧!发动机停住,伙计!叮——啊铃——铃!希特——希特——希特!”(摹仿着汽门排气的声音.)
汤姆继续刷栅栏,——不去理睬那只蒸汽轮船,本瞪着眼睛看了一会儿,说:
“哎呀,你日子好过了,是不是?”
汤姆没有回答.只是用艺术家的眼光审视他最后刷的那一块,接着轻轻地刷了一下.又
像刚才那样打量着栅栏.本走过来站在他身旁.看见那苹果,汤姆馋得直流口水,可是他还是继续刷他的墙.本说:
“嘿,老伙计,你还得干活呀,咦?”
汤姆猛然地转过身来说道:“咳!是你呀,本.我还没注意到你呢.”
“哈,告诉你吧,我可是要去游泳了.难道你不想去吗?当然啦,你宁愿在这干活,对
不对?当然你情愿!”汤姆打量了一下那男孩,说:
“你说什么?这叫干活?”
“这还不叫干活,叫干什么?”
汤姆重新又开始刷墙,漫不经心地说:“这也许是干活,也许不是.我只知道这对汤
姆·索亚来说倒是很得劲.”
“哦,得了吧!难道你的意思是说你喜欢干这事?”
刷子还在不停地刷着.
“喜欢干?哎,我真搞不懂为什么我要不喜欢干,哪个男孩子能天天有机会刷墙?”
这倒是件新鲜事.于是,本停止了啃苹果.汤姆灵巧地用刷子来回刷着——不时地停下来退后几步看看效果——在这补一刷,在那补一刷——然后再打量一下效果——本仔细地观看着汤姆的一举一动,越看越有兴趣,越看越被吸引住了.后来他说:
“喂,汤姆,让我来刷点儿看看.”
汤姆想了一下,正打算答应他;可是他立刻又改变了主意:
“不——不行,本——我想这恐怕不行.要知道,波莉姨妈对这面墙是很讲究的——这可是当街的一面呀——不过要是后面的,你刷刷倒也无妨,姨妈也不会在乎的.是呀,她对这道墙是非常讲究的.刷这墙一定得非常精心.我想在一千,也许在两千个孩子里,也找不出一个能按波莉姨妈的要求刷好这道墙的.”“哦,是吗?哎,就让我试一试吧.我只刷一
点儿——汤姆,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让你试试的.”
“本,我倒是愿意,说真的.可是,波莉姨妈——唉,吉姆想刷,可她不叫他刷,希德也想干,她也不让希德干.现在,你知道我该有多么为难?要是你来摆弄这墙,万一出了什
么毛病……”“啊,没事,我会小心仔细的.还是让我来试试吧.嘿——我把苹果核给你.”
“唉,那就……不行,本,算了吧.我就怕…….”
“我把这苹果全给你!”
汤姆把刷子让给本,脸上显示出不情愿,可心里却美滋滋的.
当刚才那只“大密苏里号”在阳光下干活,累得大汗淋漓的时候,这位离了职的艺术家却在附近的阴凉下,坐在一只木桶上,跷着二郎腿,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苹果,一边暗暗盘算如何再宰更多的傻瓜.这样的小傻瓜会有许多.每过一会儿,就有些男孩子从这经过;起先他们都想来开开玩笑,可是结果都被留下来刷墙.在本累得精疲力尽时,汤姆早已经和比
利·费施做好了交易.比利用一个修得很好的风筝换来接替本的机会.等到比利也玩得差不多的时候,詹尼·米勒用一只死老鼠和拴着它的小绳子购买了这个特权——一个又一个的傻小子受骗上了当,接连几个钟头都没有间断.下午快过了一半的时候,汤姆早上还是个贫困潦倒的穷小子,现在一下子就变成了腰包鼓鼓的阔佬了.除了以上提到的那些玩意以外,还
有十二颗石头子;一只破口琴;一块可以透视的蓝玻璃片;一门线轴做的大炮;一把什么锁也不开的钥匙;一截粉笔;一个大酒瓶塞子;一个锡皮做的小兵;一对蝌蚪;六个鞭炮;一只独眼小猫;一个门上的铜把手;一根拴狗的颈圈——却没有狗——一个刀把;四片桔子皮;还有一个破旧的窗框.
他一直过得舒舒服服,悠闲自在——同伴很多——而且墙整整被刷了三遍.要不是他的灰浆用光了的话,他会让村里的每个孩子都掏空腰包破产的.
汤姆自言自语道,这世界原来并不是那么空洞乏味啊.他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现了人类行为的一大法则——那就是为了让一个大人或一个小孩渴望干什么事,只需设法将这事变得难以到手就行了.如果他是位伟大而明智的哲学家,就像这本书的作者,他就会懂得所谓“工作”就是一个人被迫要干的事情,至于“玩”就是一个人没有义务要干的事.这个道理使他明白了为什么做假花和蹬车轮就算是工作,而玩十柱戏和爬勃朗峰就算是娱乐.英国有钱的绅士在夏季每天驾着四轮马拉客车沿着同样的路线走上二三十里,他们为这种特权竟花了很多钱.可是如果因此付钱给他们的话,那就把这桩事情变成了工作,他们就会撒手不干了.汤姆思考了一会那天发生在他身边的实质性变化,然后就到司令部报告去了 汤姆来到波莉姨妈面前,她正坐在宽敞舒适的后面房间的一个敞开的窗户旁边.这间房既是卧室、餐厅,又是图书馆.夏日芳香的空气,令人困倦的幽静,醉人的花香,还有催你入眠的嗡嗡的蜜蜂叫声,都已产生了效应,她拿着针织物在那儿打盹——因为除了只猫没有伴儿,而那猫又在她膝上睡着了.为了不打碎眼镜,她把它架在灰白的头顶上.她原以为汤姆早就溜去玩了,现在见他居然听了她的话,毫不害怕地站在她面前,不免有些诧异.他问:
“我现在可以去玩了吗?姨妈.”
“怎么,想去玩了?你刷了多少了?”
“姨妈,都刷好了.”
“汤姆,不要再跟我撒谎了——我受不了.”
“没有啊,姨妈,墙的确刷好了.”
波莉姨妈对他的话不太相信.她要亲自去看一看.只要汤姆讲的话有百分之二十是真的,她也就心满意足了.当她发现整个墙都已刷过了,不仅刷了而且是刷了一遍又一遍,甚至连地上还抹了一块,她惊讶得无法形容.她说:
“哎,真是怪事!简直叫人不可思议!汤姆,只要你想干的时候,你是挺能干的.”然后又补了一句,这一句可冲淡了刚才的表扬.“我不得不说,你想干的时候实在是太少了.好了,去玩吧,不过,别忘了到了该回来时就得回家,否则我会捶你一顿.”她为汤姆所取得的成绩而喜出望外,于是,她把他领到贮藏室,选了一个又大又好的苹果递给了他.同时还教导他,如果别人对自己的款待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而不是靠什么不德的手段谋取的,那就格外有价值,有意味.在她背了《圣经》中的一句妙语格言作结束语时,汤姆顺手牵羊偷了一块油炸面圈.
然后,他就一蹦一跳地跑出来,正好看见希德在爬通向二楼后面房间的楼梯.地上的泥块顺手可得,于是汤姆捡起泥块朝希德扔过去.这些土块像冰雹似的,在希德周围满天飞舞.波莉姨妈还没有来得及静一静她那吃惊的神经,赶紧跑过来解围,这时候,已经有六七块泥土打中了希德,而汤姆早已翻过栅栏逃之夭夭.栅栏上有大门,可是像平常一样汤姆急着要出去,没有时间从门那里走.希德让波莉姨妈注意到他的黑线,让他吃了苦头,受了罚,现在他已经对希德出了气,摆平了这件事,因此他心里觉得好受多了.
汤姆绕过那一排房子,来到靠着他姨妈牛圈后面的一条泥泞巷子里.他很快就完全地溜到抓不到也罚不着他的地方,匆忙赶到村里那块公共场地.在那里,两支由孩子们组成的“军队”按事先的约定已集合起来,准备打仗.汤姆是其中一支部队的将军,他的知心好友乔·哈帕则是另一支队伍的统帅,这两位总指挥不屑于亲自战斗——那更适合手下的军官战士去打——而他们却在一个凸出的高地方坐在一块,让他们的随从副官去发号施令,指挥打仗.经过一番长时间的艰苦奋战,汤姆的部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接着就是双方清点死亡人数,交换战俘,谈妥下次交战条件,还约定好作战日期.一切结束之后,双方部队先列好队
形,然后开拔,而汤姆也就独自回家了.
他走过杰夫·撒切尔家住的房子的时候,看见有一个新来的女孩子站在花园里——一个漂亮可爱的蓝眼睛的小姑娘.金黄色的头发梳成两只长长的发辫,身上穿着白色的夏季上装和宽松的长裤.这位刚戴上胜利花冠的战斗英雄一枪没打就束手投降了.一个叫艾美·劳伦斯的姑娘立刻从他的心目中消失了而且不留一点痕迹,他原以为他爱她爱得发狂,而且他把自己这种爱当作深情的爱慕,不过旁人看来那不过是一种可怜渺小、变幻无常的爱恋罢了.
了获取她的欢心,他费了好几个月的工夫,可她答应他还不到一个星期.他只在短短的七天内当了一次世界上最幸福、最自豪的男孩子.可现在片刻之间,她就像一位拜访完毕,告辞离去的稀客一般,从他心里离去了,消失了,被他忘得一干二净.
他爱慕这位新来的天使并偷眼望她,直到看到她发现他为止.然后,他装着她好像不在的样子,开始用各种各样可笑的孩子气的方法来炫耀自己,为的是赢得她的好感.他傻乎乎地耍弄一阵子,然后一面做惊险的体操动作,一面眼往旁边瞟了一下,见那小姑娘正朝房子走去.汤姆走到栅栏那儿,靠在栅栏上伤心,希望她再多留一阵子.她在台阶上稍作停留,然后又朝门口走去.当她抬脚上门槛时,汤姆长叹了一声.即刻他脸上又露出喜色,因为她在进去之前,向栅栏外面扔了一朵三色紫罗兰花.
汤姆跑过去停在离花一两英尺的地方,然后用手罩在眼睛上方朝街上看去,仿佛发现那边正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随后他拎起一根草杆放在鼻子上,头尽量往后仰着,极力保持着那草杆的平衡.于是,他吃力地左右移动着身体,慢慢地侧身朝那朵三色紫罗兰挪过去.最后,他的光脚落在花上,用灵巧的脚趾头抓住了它,于是,他拿着他心爱的东西,在转弯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很快就把那花别在他上衣里面贴近他心脏的地方——也许是贴近他的胃部,因为他不太懂解剖学,好在他也无所谓.
他不久又回到了老地方,在栅栏附近逛来逛去,还像原先那样耍着花样,炫耀着自己,直到天黑.虽然汤姆用一种希望安慰自己,希望她一定在窗子附近,并且已经注意到他的这番殷勤,但是,她再也没露面.后来他终于极不情愿地朝家走去,他那可怜的脑瓜子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幻想.
整个吃晚饭期间,他始终情绪高昂.他姨妈不禁感到有些纳闷:“不知这孩子怎么回事.”为了拿泥块砸希德的事,他挨了一顿臭骂,不过,对此他满不在乎.他当着姨妈的面偷糖吃,结果被她用指关节敲了一顿.他说:
“姨妈,希德拿糖吃,您怎么不打他呀.”
“噢,希德可不像你这样磨人.要不是我看得紧,你恨不得钻到糖堆里不出来.”
过了一会,她走到厨房去了;希德因为得到了特权,非常高兴,伸手去拿罐——这是故意对汤姆表示得意的一种举动,令汤姆非常难受.可是,希德手一滑,糖罐子掉到地上摔碎了.汤姆简直高兴得要命.但他闭着嘴,一言不发.他心里想他还是什么不说为好,就这么静静地坐着,等他姨妈进来,问这是谁闯的祸,那时他再说出来.看那个模范“宠儿”吃
苦头,那真是最大快人心的事.当老太太走进来,站在那儿望着地上的破碎的罐子,从眼镜上面放射出愤怒的火花,他真是高兴到了极点,几乎按捺不住了.他暗自想:“有好戏看了!”可是想不到自己反倒被打翻在地上!那只有力的巴掌举起来正要再打他时,汤姆忍不住大声叫起来:
“住手啊,你凭什么这么狠打我?——是希德打碎了糖罐!”
波莉姨妈住了手,愣了一会儿,汤姆指望她会讲些好话哄他.可是,她开口只说了这么几句:
“唉!我觉得你挨这下子也不屈.刚才,我不在的时候,说不定你又干了些别的胆大妄为的淘气事.”
然后她就受到了良心的谴责,非常想讲几句爱抚体贴的话,可是她断定这么一来,就会被认为她是在认错,这可是规矩所不容的.于是,她一声不吭,忙这忙那,可心乱如麻.汤姆坐在角落处生着气,心里越想越难受,他知道在姨妈心里,她正向他求得谅解,也就因为有这种感觉,虽然闷闷不乐但仍感到满足.他不肯挂出求和的信号,对别的表示也不去理睬.他知道有两道渴望的目光透过泪帘不时地落在他身上,可是他偏不肯表示他已经看出来.他想象着自己躺在那儿病了,快要不行了,他姨妈俯身弯腰看着他,恳求他讲一两句饶恕她的话,可是他转过脸去冲着墙,没说原谅她就死去了.啊,那时她会觉得怎么样呢?他
又想象着自己淹死了,被人从河里救起抬回家来,头上的小卷发都湿透了,他那伤透了的心得到了安息.她会多么伤心地扑到他身上,眼泪雨点般地落下来,嘴里不住地祈求上帝把她的孩子还给她,保证将永远、永远不再虐待他了!但是,他却躺在那里浑身冰凉,脸色惨白,毫无动静——一个可怜的人,一个受苦受难的人,终于结束了一切烦恼.他越想就越伤心.后来,为了嗓子不哽塞住,只好把泪水往肚子里咽.他的眼睛被泪水蒙住了,只要眼睛一眨,泪水就会淌出来,顺着鼻尖往下掉.他从这种悲伤中获得了无限的安慰和快意,所以
这时如果有什么庸俗的愉快或者什么无聊的欢乐来搅乱他的心境的话,他是绝不能忍受的.因为他这种快慰非常圣洁,不该遭到玷污.所以,一会儿之后当他的表姐玛丽手舞足蹈地跑进来的时候,他马上就避开了她.她到乡下去作客,只住了一星期,仿佛时隔三秋似的,她现在又看到自己的家,真是高兴极了.但是,当她唱着歌欢快地从一扇门走进来的时候,汤姆却站起身来乘着阴云暗影从另一扇门溜出去了.
他避开平常孩子们经常玩耍出没的地方,专找适合他此时心情的僻静地方.河里的一条木筏吸引了他,于是,他就在木筏的最外边坐下来,凝视着那单调、茫茫一片的河水,同时
又希望自己不经过老天安排的那番痛苦的过程,就一下子不知不觉地淹死.接着,他又想起了他的花,他把花拿出来,那花已经揉皱了,枯萎了,这更大大增加他凄凉而又幸福的情调.他不知道,要是她了解此事,她会不会同情他,她会哭吗?会希望有权抱住他的脖子安慰他吗?还是,她会不会像这个空洞乏味的世界一样,冷漠地掉头不管呢?这种想象给他带来一种苦中有甜的感受,于是,他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种幻想,反复地多角度地想象着,直到索然无味为止.最后,他终于叹息着站起来,在黑暗中离去.
大约在9点半或10点左右,他沿着那条没有行人的大街走着,来到那位他“爱慕的不知姓名的人”住的地方.他停下来,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却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二楼窗户的帘子上映出昏暗的烛光.那位圣洁的人儿在那儿吗?他爬过栅栏,穿过花草,悄悄地一直走到窗户下面才站住.他抬起头来,充满深情地望着窗子,看了很久.然后在窗下仰卧
在地上,双手合在胸前,捧着那朵可怜的、已经枯萎了的花.他情愿就这样死去——在这冷酷无情的世界上,当死神降临的时候,他这无家可归的人儿头上没有一丝遮盖,没有亲友的手来抹去他额上临死的汗珠,也没有慈爱的面孔贴近他来表示惋惜.就这样,当她早晨心情愉快地推开窗户,向外看时,一定会看见他的.哦!她会不会对他那可怜的、没有气息的身体落下哪怕是一小滴的泪珠呢?看见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的生命这样无情地被摧残,这样过
早地夭折,她会轻微地长叹一声吗?
窗帘卷了起来,一个女仆的说话声打破了那圣洁的寂静,随即就是一股洪水“哗”地一声泼下来,把这位躺在地上的殉情者的遗体浇得透湿!
这位被水浇得透不过气来的英雄猛地从地上爬起来,喷了喷鼻子,舒服了些.随后,只见有个什么东西混杂着一声轻轻的咒骂声,嗖地一声在空中划过,接下来就听到一阵打碎玻璃的声音,之后,就见一个小小的、模糊的人影翻过栅栏,在朦胧的夜色中箭一般地飞跑了.
不久以后,汤姆脱光衣服上床睡觉.他正借着蜡烛的光亮检查那被泼得透湿的衣服时,希德醒了.他原本有点幸灾乐祸的想法,想要“指桑骂槐”地说几句俏皮话,可是他还是改变了主意,没有出声,因为他看到汤姆眼睛里含有一股杀机.
汤姆连睡前祷告也没做就上床就睡觉了.希德在心里却记下了汤姆偷了一次懒.
大约10点30分的时候,小教堂的破钟开始响了起来,随即大家便聚集在一起听上午的布道.主日学校的孩子们各随各的父母坐在教堂里,为的是好受他们的监督.波莉姨妈来了,汤姆、希德和玛丽在她旁边坐下来.汤姆被安排在靠近过道的位子上坐着,为的是尽可能和开着的窗户及外面诱人的夏日景物离得远一些.人们簇拥着顺着过道往里走:有上了年纪的贫苦的邮政局局长,他曾经是过过好日子的;有镇长和他的太太——这地方竟然还有个镇长,这和其他许多没有必要的摆设一样;有治安法官;有道格拉斯寡妇,她40来岁,长小巧而美丽,为人宽厚,慷慨大方而又心地善良,生活还算富裕,她山上的住宅是镇上唯一漂亮讲究的,可算得上殿堂,每逢节庆日,她可是圣彼德堡镇上人们引以为荣的热情好客、最乐善好施的人;有驼背的、德高望重的华德少校和他的夫人;还有维尔逊律师,一位远道而来的新贵客.再下面就是镇上的大美人,后面跟着一大帮穿细麻布衣服、扎着缎带的、让人害单相思病的年轻姑娘.跟在她们后里的是镇上所有年轻的店员和职员,他们一涌而进——原来他们是一群如痴如醉的爱慕者,开始都站在门廊里,嘬着自己的手指头,围在那儿站成一道墙似的,一直到最后一个姑娘走出他们的包围圈为止.最后进来的一位是村里的模范儿童威利·莫夫逊,他对他母亲照顾得无微不至,就好像她是件易碎的雕花玻璃品似的.他总是领着他妈妈到教堂来,其他的妈妈都引以为豪.而男孩子们都恨他,因为他太乘巧,太听话.况且他常被人夸奖,让他们觉得难堪.他白色的手绢搭拉在屁股口袋的外面,星期天也不例外——偶而有次把除外.汤姆没有手绢,他鄙视那些有手绢的孩子们,把他们看作是故作姿态的势利小人.
听布道的人到齐后,大钟又响了一遍,为的是提醒那些迟到的和在外面乱的人.教堂里一片寂静,显得十分庄严,只有边座席上唱诗班里有些低声嘻笑和说话的声音,打破了这种寂静,而且自始至终整个布道过程,唱诗班里一直有人在窃窃私语,低声说笑.曾有过一个唱诗班不像这样没教养,可是我忘记那是在什么地方了.这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我几乎对那些事没有印象了,不过,我想大概是在外国吧.
牧师把大家要唱的歌颂主的歌词拿了出来,津津有味地念了一遍,他那特别的腔调在那地区是受人欢迎的.他的音量先由中音部开始,逐渐升高,一直升到最高音的一个字,强调了一下,然后大家一致认为他的朗诵很精彩,很美妙.在教堂的“联欢会”上,他经常被请来给大家朗诵诗文,每当他念完之后,妇女们都要举起双手,然后软绵绵地把手落下来,放在膝上,一面“转溜”着眼睛,一面摇头,好像在说:“这简直是语言无法形容的,太美了,这样动听的声音在这凡俗的人世间实在是太难得了.”
唱完颂主歌之后,牧师斯普拉格先生就把自己变成了一块布告牌,开始宣布一些集会和团体的通知之类的事情,他一直说个没完,似乎他要宣布事情就得讲个不停直到世界末日霹雳声响时才停止——这是一种很奇怪的习惯,至今在美国还保留着,甚至在当今新闻报纸很多的城市里还没有改变这种习惯.通常传统习俗越是没有多少理由存在,越很难消除它.
再后来牧师一篇很好的、内容丰富的祷告词,面面俱到:它为教堂和里面的孩子们祈祷;为全县向主求福;为漂泊在狂风暴雨的海洋上可怜的水手们求福;为被迫在欧洲君主制度和东方专制制度铁蹄下呻吟着的数万人.星期一早晨,汤姆·索亚很难受.这个时候汤姆向来是很难受的——因为又一个漫长而难熬的星期开始了.他在这一天总是想要是没有这个休息的.
再问: 你神经啦?
汤姆出现在人行道上,一只手拎着一桶灰浆,另一只手拿着一把长柄刷子.他环顾栅栏,所有的快乐,立刻烟消云散,心中充满了惆怅.栅栏可是三十码长,九英尺高啊.生活对他来说太乏味空洞了,活着仅是一种负担.他叹了一口气,用刷子蘸上灰浆,沿着最顶上一层木板刷起来.接着又刷了一下,二下.看看刚刷过的不起眼的那块,再和那远不着边际的栅栏相比,汤姆灰心丧气地在一块木箱子上坐下来.这时,吉姆手里提着一个锡皮桶,嘴中唱着“布法罗的女娃们”蹦蹦跳跳地从大门口跑出来.在汤姆眼中,到镇上从抽水机里拎水,一向件令人厌烦的差事,现在他可不这样看了.他记得在那里有很多伴儿.有白人孩
子,黑人孩子,还有混血孩子,男男女女都在那排队等着提水.大家在那儿休息,交换各自玩的东西,吵吵闹闹,争斗嬉戏.而且他还记得尽管他们家离拎水处只有一百五十码左右,可是吉姆从没有在一个小时里拎回一桶水来——有时甚至还得别人去催才行.汤姆说:
“喂,吉姆,如果你来刷点墙,我就去提水.”
吉姆摇摇头,说:
“不行,汤姆少爷.老太太,她叫我去提水,不准在路上停下来和人家玩.她说她猜到汤姆少爷你会让我刷墙,所以她吩咐我只管干自己的活,莫管他人闲事——她说她要亲自来看看你刷墙.”
“咳,吉姆,你别管她对你说的那一套.她总是这样说的.
把水桶给我——我很快就回来.她不会知道的.”
“哦,不,我可不敢,汤姆少爷.老太太她会把我的头给拧下来的,她真的会的!”
“她吗?她从来没揍过任何人——她不过是用顶针在头上敲敲罢了——谁还在乎这个,我倒是想问问你.她不过是嘴上说得凶,可是说说又伤害不了你——只要她不大叫大嚷就没事.吉姆,我给你一个好玩意,给你一个白石头子儿!”
吉姆开始动摇了.
“白石头子,吉姆!这可是真正好玩的石头子啊.”
“嘿,老实说,那是个挺不错的好玩意.可是汤姆少爷,我害怕老太太……”
“还有,吉姆,只要你答应了的话,我还给你看我那只脚趾头,那只肿痛的脚趾头.”
吉姆到底是个凡人,不是神仙——这诱惑对他太大了.他放下水桶,接过白石头子儿,还饶有兴趣地弯着腰看汤姆解开缠在脚上的布带子,看那只肿痛的脚趾.可是,一会儿之后,吉姆的屁股直痛,拎着水桶飞快地沿着街道跑掉了;汤姆继续用劲地刷墙,因为波莉姨
妈此时从田地干活回来了.她手里提着一只拖鞋,眼里流露出满意的神色.
不过,汤姆这股劲没持续多久.他开始想起原先为这个休息日所作的一些玩耍的安排,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再过一会儿,那些自由自在的孩子们就会蹦跳着跑过来,做各种各样
开心好玩的游戏,他们看到他不得不刷墙干活,会大肆嘲笑挖苦他的——一想到这,汤姆心里就像火烧似的难受.他拿出他全部的家当宝贝,仔细地看了一阵——有残缺不全的玩具、一些石头子、还有一些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这些玩意足够用来换取别的孩子为自己干活,不过,要想换来半个小时的绝对自由,也许还差得远呢.于是他又把这几件可怜的宝贝玩意
装进口袋,打消了用这些来收买那些男孩子的念头.正在这灰心绝望的时刻,他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这主意实在是聪明绝伦,妙不可言.
他拿起刷子,一声不响地干了起来.不一会儿,本·罗杰斯出现了——在所有的孩子们当中,正是这个男孩叫汤姆最害怕.汤姆最怕他的讥讽.本走路好像是做三级跳——这证明他此时的心情轻松愉快,而且还打算干点痛快高兴的事.他正在吃苹果,不时地发出长长的、好听的“呜——”的叫声,隔会儿还“叮当当、叮当当”地学铃声响,他这是在扮演一
只蒸汽轮船.他越来越近,于是他减慢速度,走到街中心,身体倾向右舷,吃力、做作地转了船头使船逆风停下——他在扮演“大密苏里号”,好像已吃水九英尺深.他既当船,又当船长还要当轮机铃.因此他就想象着自己站在轮船的顶层甲板上发着命令,同时还执行着这
些命令.
“停船,伙计!叮——啊铃!”船几乎停稳了,然后他又慢慢地向人行道靠过来.
“调转船头!叮——啊铃——铃!”他两臂伸直,用力往两边垂着.
“右舷后退,叮——啊铃——铃!嚓呜——嚓——嚓呜!嚓呜!”
他一边喊着,一边用手比划着画个大圈——这代表着一个四十英尺大转轮.
“左舷后退!叮——啊铃——铃!嚓呜——嚓——嚓呜——嚓呜!”左手开始画圈.“右舷停!叮——啊铃——铃!左舷停!右舷前进!停!外面慢慢转过来!叮——啊铃——铃!嚓——呜——呜!把船头的绳索拿过来!快点!喂——再把船边的绳索递过来——在发什么呆!把绳头靠船桩绕住好,就这么拉紧——放手吧!发动机停住,伙计!叮——啊铃——铃!希特——希特——希特!”(摹仿着汽门排气的声音.)
汤姆继续刷栅栏,——不去理睬那只蒸汽轮船,本瞪着眼睛看了一会儿,说:
“哎呀,你日子好过了,是不是?”
汤姆没有回答.只是用艺术家的眼光审视他最后刷的那一块,接着轻轻地刷了一下.又
像刚才那样打量着栅栏.本走过来站在他身旁.看见那苹果,汤姆馋得直流口水,可是他还是继续刷他的墙.本说:
“嘿,老伙计,你还得干活呀,咦?”
汤姆猛然地转过身来说道:“咳!是你呀,本.我还没注意到你呢.”
“哈,告诉你吧,我可是要去游泳了.难道你不想去吗?当然啦,你宁愿在这干活,对
不对?当然你情愿!”汤姆打量了一下那男孩,说:
“你说什么?这叫干活?”
“这还不叫干活,叫干什么?”
汤姆重新又开始刷墙,漫不经心地说:“这也许是干活,也许不是.我只知道这对汤
姆·索亚来说倒是很得劲.”
“哦,得了吧!难道你的意思是说你喜欢干这事?”
刷子还在不停地刷着.
“喜欢干?哎,我真搞不懂为什么我要不喜欢干,哪个男孩子能天天有机会刷墙?”
这倒是件新鲜事.于是,本停止了啃苹果.汤姆灵巧地用刷子来回刷着——不时地停下来退后几步看看效果——在这补一刷,在那补一刷——然后再打量一下效果——本仔细地观看着汤姆的一举一动,越看越有兴趣,越看越被吸引住了.后来他说:
“喂,汤姆,让我来刷点儿看看.”
汤姆想了一下,正打算答应他;可是他立刻又改变了主意:
“不——不行,本——我想这恐怕不行.要知道,波莉姨妈对这面墙是很讲究的——这可是当街的一面呀——不过要是后面的,你刷刷倒也无妨,姨妈也不会在乎的.是呀,她对这道墙是非常讲究的.刷这墙一定得非常精心.我想在一千,也许在两千个孩子里,也找不出一个能按波莉姨妈的要求刷好这道墙的.”“哦,是吗?哎,就让我试一试吧.我只刷一
点儿——汤姆,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让你试试的.”
“本,我倒是愿意,说真的.可是,波莉姨妈——唉,吉姆想刷,可她不叫他刷,希德也想干,她也不让希德干.现在,你知道我该有多么为难?要是你来摆弄这墙,万一出了什
么毛病……”“啊,没事,我会小心仔细的.还是让我来试试吧.嘿——我把苹果核给你.”
“唉,那就……不行,本,算了吧.我就怕…….”
“我把这苹果全给你!”
汤姆把刷子让给本,脸上显示出不情愿,可心里却美滋滋的.
当刚才那只“大密苏里号”在阳光下干活,累得大汗淋漓的时候,这位离了职的艺术家却在附近的阴凉下,坐在一只木桶上,跷着二郎腿,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苹果,一边暗暗盘算如何再宰更多的傻瓜.这样的小傻瓜会有许多.每过一会儿,就有些男孩子从这经过;起先他们都想来开开玩笑,可是结果都被留下来刷墙.在本累得精疲力尽时,汤姆早已经和比
利·费施做好了交易.比利用一个修得很好的风筝换来接替本的机会.等到比利也玩得差不多的时候,詹尼·米勒用一只死老鼠和拴着它的小绳子购买了这个特权——一个又一个的傻小子受骗上了当,接连几个钟头都没有间断.下午快过了一半的时候,汤姆早上还是个贫困潦倒的穷小子,现在一下子就变成了腰包鼓鼓的阔佬了.除了以上提到的那些玩意以外,还
有十二颗石头子;一只破口琴;一块可以透视的蓝玻璃片;一门线轴做的大炮;一把什么锁也不开的钥匙;一截粉笔;一个大酒瓶塞子;一个锡皮做的小兵;一对蝌蚪;六个鞭炮;一只独眼小猫;一个门上的铜把手;一根拴狗的颈圈——却没有狗——一个刀把;四片桔子皮;还有一个破旧的窗框.
他一直过得舒舒服服,悠闲自在——同伴很多——而且墙整整被刷了三遍.要不是他的灰浆用光了的话,他会让村里的每个孩子都掏空腰包破产的.
汤姆自言自语道,这世界原来并不是那么空洞乏味啊.他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现了人类行为的一大法则——那就是为了让一个大人或一个小孩渴望干什么事,只需设法将这事变得难以到手就行了.如果他是位伟大而明智的哲学家,就像这本书的作者,他就会懂得所谓“工作”就是一个人被迫要干的事情,至于“玩”就是一个人没有义务要干的事.这个道理使他明白了为什么做假花和蹬车轮就算是工作,而玩十柱戏和爬勃朗峰就算是娱乐.英国有钱的绅士在夏季每天驾着四轮马拉客车沿着同样的路线走上二三十里,他们为这种特权竟花了很多钱.可是如果因此付钱给他们的话,那就把这桩事情变成了工作,他们就会撒手不干了.汤姆思考了一会那天发生在他身边的实质性变化,然后就到司令部报告去了 汤姆来到波莉姨妈面前,她正坐在宽敞舒适的后面房间的一个敞开的窗户旁边.这间房既是卧室、餐厅,又是图书馆.夏日芳香的空气,令人困倦的幽静,醉人的花香,还有催你入眠的嗡嗡的蜜蜂叫声,都已产生了效应,她拿着针织物在那儿打盹——因为除了只猫没有伴儿,而那猫又在她膝上睡着了.为了不打碎眼镜,她把它架在灰白的头顶上.她原以为汤姆早就溜去玩了,现在见他居然听了她的话,毫不害怕地站在她面前,不免有些诧异.他问:
“我现在可以去玩了吗?姨妈.”
“怎么,想去玩了?你刷了多少了?”
“姨妈,都刷好了.”
“汤姆,不要再跟我撒谎了——我受不了.”
“没有啊,姨妈,墙的确刷好了.”
波莉姨妈对他的话不太相信.她要亲自去看一看.只要汤姆讲的话有百分之二十是真的,她也就心满意足了.当她发现整个墙都已刷过了,不仅刷了而且是刷了一遍又一遍,甚至连地上还抹了一块,她惊讶得无法形容.她说:
“哎,真是怪事!简直叫人不可思议!汤姆,只要你想干的时候,你是挺能干的.”然后又补了一句,这一句可冲淡了刚才的表扬.“我不得不说,你想干的时候实在是太少了.好了,去玩吧,不过,别忘了到了该回来时就得回家,否则我会捶你一顿.”她为汤姆所取得的成绩而喜出望外,于是,她把他领到贮藏室,选了一个又大又好的苹果递给了他.同时还教导他,如果别人对自己的款待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而不是靠什么不德的手段谋取的,那就格外有价值,有意味.在她背了《圣经》中的一句妙语格言作结束语时,汤姆顺手牵羊偷了一块油炸面圈.
然后,他就一蹦一跳地跑出来,正好看见希德在爬通向二楼后面房间的楼梯.地上的泥块顺手可得,于是汤姆捡起泥块朝希德扔过去.这些土块像冰雹似的,在希德周围满天飞舞.波莉姨妈还没有来得及静一静她那吃惊的神经,赶紧跑过来解围,这时候,已经有六七块泥土打中了希德,而汤姆早已翻过栅栏逃之夭夭.栅栏上有大门,可是像平常一样汤姆急着要出去,没有时间从门那里走.希德让波莉姨妈注意到他的黑线,让他吃了苦头,受了罚,现在他已经对希德出了气,摆平了这件事,因此他心里觉得好受多了.
汤姆绕过那一排房子,来到靠着他姨妈牛圈后面的一条泥泞巷子里.他很快就完全地溜到抓不到也罚不着他的地方,匆忙赶到村里那块公共场地.在那里,两支由孩子们组成的“军队”按事先的约定已集合起来,准备打仗.汤姆是其中一支部队的将军,他的知心好友乔·哈帕则是另一支队伍的统帅,这两位总指挥不屑于亲自战斗——那更适合手下的军官战士去打——而他们却在一个凸出的高地方坐在一块,让他们的随从副官去发号施令,指挥打仗.经过一番长时间的艰苦奋战,汤姆的部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接着就是双方清点死亡人数,交换战俘,谈妥下次交战条件,还约定好作战日期.一切结束之后,双方部队先列好队
形,然后开拔,而汤姆也就独自回家了.
他走过杰夫·撒切尔家住的房子的时候,看见有一个新来的女孩子站在花园里——一个漂亮可爱的蓝眼睛的小姑娘.金黄色的头发梳成两只长长的发辫,身上穿着白色的夏季上装和宽松的长裤.这位刚戴上胜利花冠的战斗英雄一枪没打就束手投降了.一个叫艾美·劳伦斯的姑娘立刻从他的心目中消失了而且不留一点痕迹,他原以为他爱她爱得发狂,而且他把自己这种爱当作深情的爱慕,不过旁人看来那不过是一种可怜渺小、变幻无常的爱恋罢了.
了获取她的欢心,他费了好几个月的工夫,可她答应他还不到一个星期.他只在短短的七天内当了一次世界上最幸福、最自豪的男孩子.可现在片刻之间,她就像一位拜访完毕,告辞离去的稀客一般,从他心里离去了,消失了,被他忘得一干二净.
他爱慕这位新来的天使并偷眼望她,直到看到她发现他为止.然后,他装着她好像不在的样子,开始用各种各样可笑的孩子气的方法来炫耀自己,为的是赢得她的好感.他傻乎乎地耍弄一阵子,然后一面做惊险的体操动作,一面眼往旁边瞟了一下,见那小姑娘正朝房子走去.汤姆走到栅栏那儿,靠在栅栏上伤心,希望她再多留一阵子.她在台阶上稍作停留,然后又朝门口走去.当她抬脚上门槛时,汤姆长叹了一声.即刻他脸上又露出喜色,因为她在进去之前,向栅栏外面扔了一朵三色紫罗兰花.
汤姆跑过去停在离花一两英尺的地方,然后用手罩在眼睛上方朝街上看去,仿佛发现那边正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随后他拎起一根草杆放在鼻子上,头尽量往后仰着,极力保持着那草杆的平衡.于是,他吃力地左右移动着身体,慢慢地侧身朝那朵三色紫罗兰挪过去.最后,他的光脚落在花上,用灵巧的脚趾头抓住了它,于是,他拿着他心爱的东西,在转弯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很快就把那花别在他上衣里面贴近他心脏的地方——也许是贴近他的胃部,因为他不太懂解剖学,好在他也无所谓.
他不久又回到了老地方,在栅栏附近逛来逛去,还像原先那样耍着花样,炫耀着自己,直到天黑.虽然汤姆用一种希望安慰自己,希望她一定在窗子附近,并且已经注意到他的这番殷勤,但是,她再也没露面.后来他终于极不情愿地朝家走去,他那可怜的脑瓜子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幻想.
整个吃晚饭期间,他始终情绪高昂.他姨妈不禁感到有些纳闷:“不知这孩子怎么回事.”为了拿泥块砸希德的事,他挨了一顿臭骂,不过,对此他满不在乎.他当着姨妈的面偷糖吃,结果被她用指关节敲了一顿.他说:
“姨妈,希德拿糖吃,您怎么不打他呀.”
“噢,希德可不像你这样磨人.要不是我看得紧,你恨不得钻到糖堆里不出来.”
过了一会,她走到厨房去了;希德因为得到了特权,非常高兴,伸手去拿罐——这是故意对汤姆表示得意的一种举动,令汤姆非常难受.可是,希德手一滑,糖罐子掉到地上摔碎了.汤姆简直高兴得要命.但他闭着嘴,一言不发.他心里想他还是什么不说为好,就这么静静地坐着,等他姨妈进来,问这是谁闯的祸,那时他再说出来.看那个模范“宠儿”吃
苦头,那真是最大快人心的事.当老太太走进来,站在那儿望着地上的破碎的罐子,从眼镜上面放射出愤怒的火花,他真是高兴到了极点,几乎按捺不住了.他暗自想:“有好戏看了!”可是想不到自己反倒被打翻在地上!那只有力的巴掌举起来正要再打他时,汤姆忍不住大声叫起来:
“住手啊,你凭什么这么狠打我?——是希德打碎了糖罐!”
波莉姨妈住了手,愣了一会儿,汤姆指望她会讲些好话哄他.可是,她开口只说了这么几句:
“唉!我觉得你挨这下子也不屈.刚才,我不在的时候,说不定你又干了些别的胆大妄为的淘气事.”
然后她就受到了良心的谴责,非常想讲几句爱抚体贴的话,可是她断定这么一来,就会被认为她是在认错,这可是规矩所不容的.于是,她一声不吭,忙这忙那,可心乱如麻.汤姆坐在角落处生着气,心里越想越难受,他知道在姨妈心里,她正向他求得谅解,也就因为有这种感觉,虽然闷闷不乐但仍感到满足.他不肯挂出求和的信号,对别的表示也不去理睬.他知道有两道渴望的目光透过泪帘不时地落在他身上,可是他偏不肯表示他已经看出来.他想象着自己躺在那儿病了,快要不行了,他姨妈俯身弯腰看着他,恳求他讲一两句饶恕她的话,可是他转过脸去冲着墙,没说原谅她就死去了.啊,那时她会觉得怎么样呢?他
又想象着自己淹死了,被人从河里救起抬回家来,头上的小卷发都湿透了,他那伤透了的心得到了安息.她会多么伤心地扑到他身上,眼泪雨点般地落下来,嘴里不住地祈求上帝把她的孩子还给她,保证将永远、永远不再虐待他了!但是,他却躺在那里浑身冰凉,脸色惨白,毫无动静——一个可怜的人,一个受苦受难的人,终于结束了一切烦恼.他越想就越伤心.后来,为了嗓子不哽塞住,只好把泪水往肚子里咽.他的眼睛被泪水蒙住了,只要眼睛一眨,泪水就会淌出来,顺着鼻尖往下掉.他从这种悲伤中获得了无限的安慰和快意,所以
这时如果有什么庸俗的愉快或者什么无聊的欢乐来搅乱他的心境的话,他是绝不能忍受的.因为他这种快慰非常圣洁,不该遭到玷污.所以,一会儿之后当他的表姐玛丽手舞足蹈地跑进来的时候,他马上就避开了她.她到乡下去作客,只住了一星期,仿佛时隔三秋似的,她现在又看到自己的家,真是高兴极了.但是,当她唱着歌欢快地从一扇门走进来的时候,汤姆却站起身来乘着阴云暗影从另一扇门溜出去了.
他避开平常孩子们经常玩耍出没的地方,专找适合他此时心情的僻静地方.河里的一条木筏吸引了他,于是,他就在木筏的最外边坐下来,凝视着那单调、茫茫一片的河水,同时
又希望自己不经过老天安排的那番痛苦的过程,就一下子不知不觉地淹死.接着,他又想起了他的花,他把花拿出来,那花已经揉皱了,枯萎了,这更大大增加他凄凉而又幸福的情调.他不知道,要是她了解此事,她会不会同情他,她会哭吗?会希望有权抱住他的脖子安慰他吗?还是,她会不会像这个空洞乏味的世界一样,冷漠地掉头不管呢?这种想象给他带来一种苦中有甜的感受,于是,他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种幻想,反复地多角度地想象着,直到索然无味为止.最后,他终于叹息着站起来,在黑暗中离去.
大约在9点半或10点左右,他沿着那条没有行人的大街走着,来到那位他“爱慕的不知姓名的人”住的地方.他停下来,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却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二楼窗户的帘子上映出昏暗的烛光.那位圣洁的人儿在那儿吗?他爬过栅栏,穿过花草,悄悄地一直走到窗户下面才站住.他抬起头来,充满深情地望着窗子,看了很久.然后在窗下仰卧
在地上,双手合在胸前,捧着那朵可怜的、已经枯萎了的花.他情愿就这样死去——在这冷酷无情的世界上,当死神降临的时候,他这无家可归的人儿头上没有一丝遮盖,没有亲友的手来抹去他额上临死的汗珠,也没有慈爱的面孔贴近他来表示惋惜.就这样,当她早晨心情愉快地推开窗户,向外看时,一定会看见他的.哦!她会不会对他那可怜的、没有气息的身体落下哪怕是一小滴的泪珠呢?看见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的生命这样无情地被摧残,这样过
早地夭折,她会轻微地长叹一声吗?
窗帘卷了起来,一个女仆的说话声打破了那圣洁的寂静,随即就是一股洪水“哗”地一声泼下来,把这位躺在地上的殉情者的遗体浇得透湿!
这位被水浇得透不过气来的英雄猛地从地上爬起来,喷了喷鼻子,舒服了些.随后,只见有个什么东西混杂着一声轻轻的咒骂声,嗖地一声在空中划过,接下来就听到一阵打碎玻璃的声音,之后,就见一个小小的、模糊的人影翻过栅栏,在朦胧的夜色中箭一般地飞跑了.
不久以后,汤姆脱光衣服上床睡觉.他正借着蜡烛的光亮检查那被泼得透湿的衣服时,希德醒了.他原本有点幸灾乐祸的想法,想要“指桑骂槐”地说几句俏皮话,可是他还是改变了主意,没有出声,因为他看到汤姆眼睛里含有一股杀机.
汤姆连睡前祷告也没做就上床就睡觉了.希德在心里却记下了汤姆偷了一次懒.
大约10点30分的时候,小教堂的破钟开始响了起来,随即大家便聚集在一起听上午的布道.主日学校的孩子们各随各的父母坐在教堂里,为的是好受他们的监督.波莉姨妈来了,汤姆、希德和玛丽在她旁边坐下来.汤姆被安排在靠近过道的位子上坐着,为的是尽可能和开着的窗户及外面诱人的夏日景物离得远一些.人们簇拥着顺着过道往里走:有上了年纪的贫苦的邮政局局长,他曾经是过过好日子的;有镇长和他的太太——这地方竟然还有个镇长,这和其他许多没有必要的摆设一样;有治安法官;有道格拉斯寡妇,她40来岁,长小巧而美丽,为人宽厚,慷慨大方而又心地善良,生活还算富裕,她山上的住宅是镇上唯一漂亮讲究的,可算得上殿堂,每逢节庆日,她可是圣彼德堡镇上人们引以为荣的热情好客、最乐善好施的人;有驼背的、德高望重的华德少校和他的夫人;还有维尔逊律师,一位远道而来的新贵客.再下面就是镇上的大美人,后面跟着一大帮穿细麻布衣服、扎着缎带的、让人害单相思病的年轻姑娘.跟在她们后里的是镇上所有年轻的店员和职员,他们一涌而进——原来他们是一群如痴如醉的爱慕者,开始都站在门廊里,嘬着自己的手指头,围在那儿站成一道墙似的,一直到最后一个姑娘走出他们的包围圈为止.最后进来的一位是村里的模范儿童威利·莫夫逊,他对他母亲照顾得无微不至,就好像她是件易碎的雕花玻璃品似的.他总是领着他妈妈到教堂来,其他的妈妈都引以为豪.而男孩子们都恨他,因为他太乘巧,太听话.况且他常被人夸奖,让他们觉得难堪.他白色的手绢搭拉在屁股口袋的外面,星期天也不例外——偶而有次把除外.汤姆没有手绢,他鄙视那些有手绢的孩子们,把他们看作是故作姿态的势利小人.
听布道的人到齐后,大钟又响了一遍,为的是提醒那些迟到的和在外面乱的人.教堂里一片寂静,显得十分庄严,只有边座席上唱诗班里有些低声嘻笑和说话的声音,打破了这种寂静,而且自始至终整个布道过程,唱诗班里一直有人在窃窃私语,低声说笑.曾有过一个唱诗班不像这样没教养,可是我忘记那是在什么地方了.这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我几乎对那些事没有印象了,不过,我想大概是在外国吧.
牧师把大家要唱的歌颂主的歌词拿了出来,津津有味地念了一遍,他那特别的腔调在那地区是受人欢迎的.他的音量先由中音部开始,逐渐升高,一直升到最高音的一个字,强调了一下,然后大家一致认为他的朗诵很精彩,很美妙.在教堂的“联欢会”上,他经常被请来给大家朗诵诗文,每当他念完之后,妇女们都要举起双手,然后软绵绵地把手落下来,放在膝上,一面“转溜”着眼睛,一面摇头,好像在说:“这简直是语言无法形容的,太美了,这样动听的声音在这凡俗的人世间实在是太难得了.”
唱完颂主歌之后,牧师斯普拉格先生就把自己变成了一块布告牌,开始宣布一些集会和团体的通知之类的事情,他一直说个没完,似乎他要宣布事情就得讲个不停直到世界末日霹雳声响时才停止——这是一种很奇怪的习惯,至今在美国还保留着,甚至在当今新闻报纸很多的城市里还没有改变这种习惯.通常传统习俗越是没有多少理由存在,越很难消除它.
再后来牧师一篇很好的、内容丰富的祷告词,面面俱到:它为教堂和里面的孩子们祈祷;为全县向主求福;为漂泊在狂风暴雨的海洋上可怜的水手们求福;为被迫在欧洲君主制度和东方专制制度铁蹄下呻吟着的数万人.星期一早晨,汤姆·索亚很难受.这个时候汤姆向来是很难受的——因为又一个漫长而难熬的星期开始了.他在这一天总是想要是没有这个休息的.
再问: 你神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