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扬娜拉的日本女郎是什么模样,性格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神马作文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11/16 18:15:23
沙扬娜拉的日本女郎是什么模样,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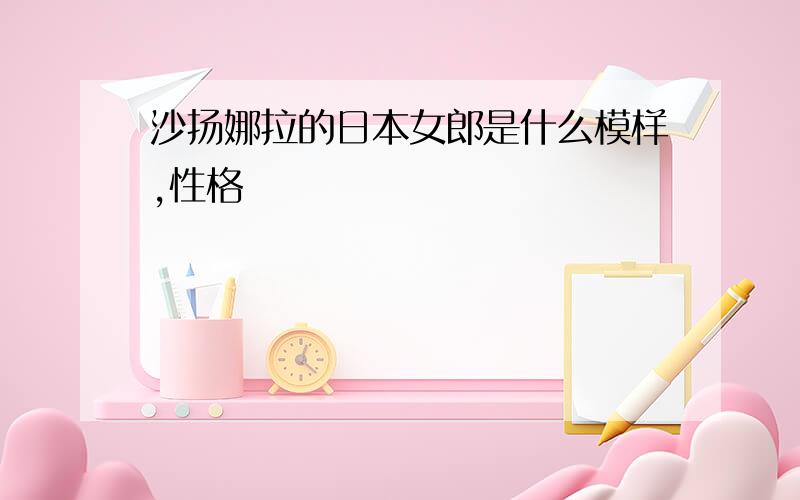
沙扬娜拉
徐志摩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
沙扬娜拉!
赏析:
徐志摩的小诗《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短短五句,却包融了无限的离绪和柔情.以一朵不胜娇羞的水莲状写日本女郎温柔的神态,贴切传神,既纯洁无瑕,又楚楚动人.一声“沙扬娜拉”,轻飘而不尖深沉,随意而不失执著,简洁而又充满异国情调.这首诗充分显示出诗人徐志摩善于勾勒,巧于传情,以及他驾驭语言的非凡功力.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不论是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还是文学作品的情感性,都是通过对语言及其形式的感受 理解获得的.脱离开对语言及其形式的感受和理解,思想性就是一些抽象的教条,情感性就是一些空洞的抒情.这样的思想性和情感性严格说来还不是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情感性.所以,我们语文教学的任务,首先是引导学生 受和理解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及其形式,过去 种跨越语言直取思想、直取情感的方式是要 得的.
诗歌是一种更纯粹的语言艺术,它没有小说的虚构的故事情节;没有散文的具体的事件和人 ,更没有戏剧的舞台演出,我们在诗歌中接触的几乎只有语言,我们对诗歌的感受和理解,主要是对诗歌语言的感受和 解.所以,在诗歌的教学中, 导学生感受和理解诗歌的语言几乎是惟一重要的教学内容.
在这里, 想通过徐志摩的《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一诗的赏析说明这个问题.
在徐志摩这首小诗里,几乎没有对人物的细致描写,也没有对人物心理的着意刻划,更没有作者情感的直接表现.但所有这一切,在我们每个读者的感 里却是异常清晰明确的.首先,我们不会认为这个日本女郎有着修长的身材,有着西方女性常有的结实的肌肉和健壮的体魄,但她也不是矮小的,瘦弱的,而是娇小而 满的;她的脸色不是红润的,但也不是苍白的,而是白皙光洁的;她穿的衣服不是紧身的、把身体的每一个曲线都能够 露出来的现代西方的服装,但也不是臃肿得无法感到女性的曲线美的那种只有老太婆才爱穿的衣服;她的服装的颜色不是鲜艳的红色和绿色,但也不是朴实无华的蓝色或灰色;她不华贵,但也不粗俗;不矜持,但也不放荡……那么,这么一个日本少女的形象我们是怎样感觉出来的呢?我们不是仅仅从徐志 对这个日本女郎的具体描写中感觉出来的,而更是从对这首诗、对这首诗的语言的感觉中感觉出来的.我们简直可以说,这首诗的本身就是这个日本女郎的形象.它小而美,构成的也正是这个 本女郎娇小而美丽的 体的形象.它使我们想像不出一个修长硕大的身躯来.“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写的是这个日本女郎的“温柔”,写的是她微微低头时给人的温柔、温馨的感觉,但是,仅有这样的描写,还是无法构成这个日本女郎的整体的温柔、温馨的形象的.这个日本女郎温柔、温馨的形象更是从全诗语言的“温柔”中实际感到的.我们可以看到,全诗没有一个像铁、石这样一些给人 来沉重感、冷硬感的词语,也没有像辉煌、昂扬这样响亮的词语,只有“珍重”的“重”字可以给人带来沉重感,但它在“珍重”一词里处在轻音的位置上,读出来的“珍重”这个词给人的却是关切的、温暖的感觉.“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这种反复的致意,并且是从一个美丽的日本少女的口里徐徐地吐露出来,给人的感觉就更加 暖和温馨.“凉风”在词义上是 凉”的,但读起来却并不感到凉意,倒像是更加衬托出了全诗给人的温暖.全诗的每一个词都好像没有多么大的重量,每一个音都不会给人产生强烈的刺激,它押的是“OU”韵,而“OU”韵则既不是太响亮的,也不是太沉闷的,它本身就给人一种舒服的、温柔的感觉.只要我们反复读一读这首诗,我们就会感到这首诗的语言在整体上就是温柔、温馨的.我们感受着 首诗的语言,同时也是在感受着这个日本女郎的身体形象,它托住了我们的温柔的、温馨的感觉,同时也托住了这个日本女郎的温柔的、温馨的形象 ——我们是在这首诗的语言给我们的心灵感觉里想像这个日本女郎的具体的身体形象的.
在徐志摩这首小诗的语流中,“最”字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不仅把作者对这个日本女郎“一低头”的神态的心灵感触突出了出来,而且在全诗中是惟一一个短促的收口音,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力度感,它突如其来,好像轻轻地推了我们一下,一下子把我们推到了这首小诗的世界里,推到了这个日本女郎的面前.起到的是“无”中生“有”的作用.“最”字以后的所有字词,几乎都是有尾音的音,这种尾音把前一个音与后一个音很自然地联 在一起,整首诗除了在一个句子结束时有一个轻轻的停顿之外,其它语词都呈现着一种连绵不断的变化状态,它不像“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闻一多:《死水》)一样是一个词一个词地绝然地顿开的,也不像“ 冷清清,戚戚惨惨戚戚”(李清照:《声声慢:“冷冷清清”》)一样是前后重叠、在一个音或相近 音上蹉跎盘旋的,它时时变化着,但我们却感觉不到它的转折性的变化,从一个音向另一个音的过渡都非常自然,往往是上一个音的结束正好易于下一个音的发音,不用重新调整发音的部位.没有佶屈聱牙感,没有不能不绝然顿开的地方,整首诗的语言,都使我们感到一种轻柔的曲线美,一种轻盈感,一种飘逸感.这种轻柔的曲线美,这种轻盈感,这种飘逸感,也是我们在想像中重构这个日本女郎形象的心理基础.所以,我们想像中的日本女郎,绝不会是西方那种健美女郎的形象,也不是中国古代那种瘦弱多病的贵族女郎的形象;她穿的 是西方绽露着身体的每一条曲线的紧身衣,也不是根本无法表现女性身体曲线美的臃肿厚重的衣服,而是相对宽松但却有着轻盈感、飘逸感的日本和服.
在这首诗里,只出现了两种色彩:白和红.白是水莲花那种滋润、致密、光洁的“白”,红是在水莲花整体滋润、致密、光洁的白色的底色上透露出的微微的、淡淡的、浅浅的红色.“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直接把“水莲花”和这个日本女郎连接起来、等同起来,“像一朵水莲花”是用水莲花比喻这个日本女郎,不胜凉风的“娇羞”则 是用这个日本女郎的颜面比喻水莲花,这就把水莲花和这个日本女郎的形象同时表现出来.实际上,整首诗的其它语言是一种无色之色,不论看起来还是读起来,读者都能感到它在整体上 清淡和纯净,而不会产生浑浊、芜杂的感觉.必须看到,这种色彩感呈现了这个日本女郎的面容,同时也呈现了她的整体形象.她光洁照人, 素洁中透露着内在的美艳,在幽静中传达出内心的情意.她的衣服的颜色不是鲜艳夺目的大红和大绿,不是给人阴沉感的黑色,不是毫无光彩的灰色,也不是带有圣洁感的蓝色,而是在素的,淡的,光洁的底色上很自然地点缀着其它艳丽的色彩.她是纯洁的,但不是圣洁的;她是一种世俗的美,但 低俗和庸俗.她有一颗纯净的心灵,但也有一个少女的敏感的心灵和活跃着的感情.
在过去,我们曾经争论过徐志摩这首诗到底是不是“爱情诗”,我认为,这正是我们过去常常脱离开语言的感觉而直取思想、直取感情的结果. 若我们重视的不是理性判断中的思想或感情,而是对诗歌语言的感受和理解,我们就不会产生它是不是爱情诗的问题.实际上,在这首诗里,不论是这个日本女郎还是诗人本人,都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什么,都没有想到自己爱还是不爱对 .这里写的只是一点感觉,一点一闪而过、一瞬既逝的感觉,一点似有实无、似无实有、谁也无法用明确的语言进行表达的刹那的感觉.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它才成了诗,成了一首脍 人口的小诗.它把人们用理性语言很难传达的情感和很难述说的情景表达出来.日本女郎 上呈现出的那点“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语气里的那点“蜜甜的忧愁”,都在可见而不可见之间传达出了日本女郎内心的那点情感的悸动,但在这娇羞中又有一点凉意,在这忧愁中又有 甜蜜,娇羞透露出她对送别中的诗人的一点无意识的爱意、一点刹那浮现的情感,这种情感在送别以前未曾发生,在送别之后也不会继续发展.凉意则传达着她不会、不能也不想留住对方、留住自己这点情感的无意识中的失落感觉;甜蜜是由于这点爱意感觉,忧愁也是因为这点爱意感觉,爱意感觉本身就是甜蜜的,但这种感觉发生在送别时则不能不感到一点忧愁.所有这一切, 只发生在送别的这一刹那,仅在这一刹那的感受和回忆中保存着,没有过程,也没有发展,没有消失,也没有加强.对于这个日本女郎是这样,对于诗人也是这样.诗人的那点情,那点温馨的感觉和那点“蜜甜的忧愁”,全都包容在他对日本女郎 “一低头的温柔”的“最是”的感觉中,全都包容在他对那个日本女郎“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的语气里那点“蜜甜的忧愁”的敏感中,正是他对这个日本女郎在送别的一刹那也有了一点莫 的爱意,所以他才从这个日本女郎的一低头中感到了温柔,在她的道别的语气中感到了“蜜甜”和“忧愁”.这里的“蜜甜”和“忧愁”,既是日本女郎的语气中所有,也是诗人自己的内心感觉.在这时,两个人的那点情意都是不自觉的,都是一瞬即逝的,但却在刹那间实现了彼此的沟通,发生了无言中的交流.我们所感到的温馨,我们所感觉到的美,恐怕就在这刹那的两心相遇吧.至于日本女郎那 “不胜凉风的娇羞”、那点“蜜甜的忧愁”,至于诗人那点温柔的感觉,那点与日本女郎相同的“蜜甜的忧愁”是不是“爱情”,对我们又有什么重要呢?只要我们重视对诗的语言的实际感受和理解,我们就会感到,“爱情”这个词对于这首诗太大、太重、太严肃了.
总之,文学的语言是有质感的语言 是可以用心灵触摸的语言,是可以摸到硬度、掂出重量、看到颜色的语言.语文教学要不断加强学生对我们民族语言的这种质感的感觉,学生感受、理解和运用我们民族语言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我们民族语言的质感感觉的能力的提高上.
徐志摩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
沙扬娜拉!
赏析:
徐志摩的小诗《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短短五句,却包融了无限的离绪和柔情.以一朵不胜娇羞的水莲状写日本女郎温柔的神态,贴切传神,既纯洁无瑕,又楚楚动人.一声“沙扬娜拉”,轻飘而不尖深沉,随意而不失执著,简洁而又充满异国情调.这首诗充分显示出诗人徐志摩善于勾勒,巧于传情,以及他驾驭语言的非凡功力.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不论是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还是文学作品的情感性,都是通过对语言及其形式的感受 理解获得的.脱离开对语言及其形式的感受和理解,思想性就是一些抽象的教条,情感性就是一些空洞的抒情.这样的思想性和情感性严格说来还不是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情感性.所以,我们语文教学的任务,首先是引导学生 受和理解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及其形式,过去 种跨越语言直取思想、直取情感的方式是要 得的.
诗歌是一种更纯粹的语言艺术,它没有小说的虚构的故事情节;没有散文的具体的事件和人 ,更没有戏剧的舞台演出,我们在诗歌中接触的几乎只有语言,我们对诗歌的感受和理解,主要是对诗歌语言的感受和 解.所以,在诗歌的教学中, 导学生感受和理解诗歌的语言几乎是惟一重要的教学内容.
在这里, 想通过徐志摩的《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一诗的赏析说明这个问题.
在徐志摩这首小诗里,几乎没有对人物的细致描写,也没有对人物心理的着意刻划,更没有作者情感的直接表现.但所有这一切,在我们每个读者的感 里却是异常清晰明确的.首先,我们不会认为这个日本女郎有着修长的身材,有着西方女性常有的结实的肌肉和健壮的体魄,但她也不是矮小的,瘦弱的,而是娇小而 满的;她的脸色不是红润的,但也不是苍白的,而是白皙光洁的;她穿的衣服不是紧身的、把身体的每一个曲线都能够 露出来的现代西方的服装,但也不是臃肿得无法感到女性的曲线美的那种只有老太婆才爱穿的衣服;她的服装的颜色不是鲜艳的红色和绿色,但也不是朴实无华的蓝色或灰色;她不华贵,但也不粗俗;不矜持,但也不放荡……那么,这么一个日本少女的形象我们是怎样感觉出来的呢?我们不是仅仅从徐志 对这个日本女郎的具体描写中感觉出来的,而更是从对这首诗、对这首诗的语言的感觉中感觉出来的.我们简直可以说,这首诗的本身就是这个日本女郎的形象.它小而美,构成的也正是这个 本女郎娇小而美丽的 体的形象.它使我们想像不出一个修长硕大的身躯来.“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写的是这个日本女郎的“温柔”,写的是她微微低头时给人的温柔、温馨的感觉,但是,仅有这样的描写,还是无法构成这个日本女郎的整体的温柔、温馨的形象的.这个日本女郎温柔、温馨的形象更是从全诗语言的“温柔”中实际感到的.我们可以看到,全诗没有一个像铁、石这样一些给人 来沉重感、冷硬感的词语,也没有像辉煌、昂扬这样响亮的词语,只有“珍重”的“重”字可以给人带来沉重感,但它在“珍重”一词里处在轻音的位置上,读出来的“珍重”这个词给人的却是关切的、温暖的感觉.“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这种反复的致意,并且是从一个美丽的日本少女的口里徐徐地吐露出来,给人的感觉就更加 暖和温馨.“凉风”在词义上是 凉”的,但读起来却并不感到凉意,倒像是更加衬托出了全诗给人的温暖.全诗的每一个词都好像没有多么大的重量,每一个音都不会给人产生强烈的刺激,它押的是“OU”韵,而“OU”韵则既不是太响亮的,也不是太沉闷的,它本身就给人一种舒服的、温柔的感觉.只要我们反复读一读这首诗,我们就会感到这首诗的语言在整体上就是温柔、温馨的.我们感受着 首诗的语言,同时也是在感受着这个日本女郎的身体形象,它托住了我们的温柔的、温馨的感觉,同时也托住了这个日本女郎的温柔的、温馨的形象 ——我们是在这首诗的语言给我们的心灵感觉里想像这个日本女郎的具体的身体形象的.
在徐志摩这首小诗的语流中,“最”字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不仅把作者对这个日本女郎“一低头”的神态的心灵感触突出了出来,而且在全诗中是惟一一个短促的收口音,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力度感,它突如其来,好像轻轻地推了我们一下,一下子把我们推到了这首小诗的世界里,推到了这个日本女郎的面前.起到的是“无”中生“有”的作用.“最”字以后的所有字词,几乎都是有尾音的音,这种尾音把前一个音与后一个音很自然地联 在一起,整首诗除了在一个句子结束时有一个轻轻的停顿之外,其它语词都呈现着一种连绵不断的变化状态,它不像“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闻一多:《死水》)一样是一个词一个词地绝然地顿开的,也不像“ 冷清清,戚戚惨惨戚戚”(李清照:《声声慢:“冷冷清清”》)一样是前后重叠、在一个音或相近 音上蹉跎盘旋的,它时时变化着,但我们却感觉不到它的转折性的变化,从一个音向另一个音的过渡都非常自然,往往是上一个音的结束正好易于下一个音的发音,不用重新调整发音的部位.没有佶屈聱牙感,没有不能不绝然顿开的地方,整首诗的语言,都使我们感到一种轻柔的曲线美,一种轻盈感,一种飘逸感.这种轻柔的曲线美,这种轻盈感,这种飘逸感,也是我们在想像中重构这个日本女郎形象的心理基础.所以,我们想像中的日本女郎,绝不会是西方那种健美女郎的形象,也不是中国古代那种瘦弱多病的贵族女郎的形象;她穿的 是西方绽露着身体的每一条曲线的紧身衣,也不是根本无法表现女性身体曲线美的臃肿厚重的衣服,而是相对宽松但却有着轻盈感、飘逸感的日本和服.
在这首诗里,只出现了两种色彩:白和红.白是水莲花那种滋润、致密、光洁的“白”,红是在水莲花整体滋润、致密、光洁的白色的底色上透露出的微微的、淡淡的、浅浅的红色.“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直接把“水莲花”和这个日本女郎连接起来、等同起来,“像一朵水莲花”是用水莲花比喻这个日本女郎,不胜凉风的“娇羞”则 是用这个日本女郎的颜面比喻水莲花,这就把水莲花和这个日本女郎的形象同时表现出来.实际上,整首诗的其它语言是一种无色之色,不论看起来还是读起来,读者都能感到它在整体上 清淡和纯净,而不会产生浑浊、芜杂的感觉.必须看到,这种色彩感呈现了这个日本女郎的面容,同时也呈现了她的整体形象.她光洁照人, 素洁中透露着内在的美艳,在幽静中传达出内心的情意.她的衣服的颜色不是鲜艳夺目的大红和大绿,不是给人阴沉感的黑色,不是毫无光彩的灰色,也不是带有圣洁感的蓝色,而是在素的,淡的,光洁的底色上很自然地点缀着其它艳丽的色彩.她是纯洁的,但不是圣洁的;她是一种世俗的美,但 低俗和庸俗.她有一颗纯净的心灵,但也有一个少女的敏感的心灵和活跃着的感情.
在过去,我们曾经争论过徐志摩这首诗到底是不是“爱情诗”,我认为,这正是我们过去常常脱离开语言的感觉而直取思想、直取感情的结果. 若我们重视的不是理性判断中的思想或感情,而是对诗歌语言的感受和理解,我们就不会产生它是不是爱情诗的问题.实际上,在这首诗里,不论是这个日本女郎还是诗人本人,都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什么,都没有想到自己爱还是不爱对 .这里写的只是一点感觉,一点一闪而过、一瞬既逝的感觉,一点似有实无、似无实有、谁也无法用明确的语言进行表达的刹那的感觉.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它才成了诗,成了一首脍 人口的小诗.它把人们用理性语言很难传达的情感和很难述说的情景表达出来.日本女郎 上呈现出的那点“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语气里的那点“蜜甜的忧愁”,都在可见而不可见之间传达出了日本女郎内心的那点情感的悸动,但在这娇羞中又有一点凉意,在这忧愁中又有 甜蜜,娇羞透露出她对送别中的诗人的一点无意识的爱意、一点刹那浮现的情感,这种情感在送别以前未曾发生,在送别之后也不会继续发展.凉意则传达着她不会、不能也不想留住对方、留住自己这点情感的无意识中的失落感觉;甜蜜是由于这点爱意感觉,忧愁也是因为这点爱意感觉,爱意感觉本身就是甜蜜的,但这种感觉发生在送别时则不能不感到一点忧愁.所有这一切, 只发生在送别的这一刹那,仅在这一刹那的感受和回忆中保存着,没有过程,也没有发展,没有消失,也没有加强.对于这个日本女郎是这样,对于诗人也是这样.诗人的那点情,那点温馨的感觉和那点“蜜甜的忧愁”,全都包容在他对日本女郎 “一低头的温柔”的“最是”的感觉中,全都包容在他对那个日本女郎“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的语气里那点“蜜甜的忧愁”的敏感中,正是他对这个日本女郎在送别的一刹那也有了一点莫 的爱意,所以他才从这个日本女郎的一低头中感到了温柔,在她的道别的语气中感到了“蜜甜”和“忧愁”.这里的“蜜甜”和“忧愁”,既是日本女郎的语气中所有,也是诗人自己的内心感觉.在这时,两个人的那点情意都是不自觉的,都是一瞬即逝的,但却在刹那间实现了彼此的沟通,发生了无言中的交流.我们所感到的温馨,我们所感觉到的美,恐怕就在这刹那的两心相遇吧.至于日本女郎那 “不胜凉风的娇羞”、那点“蜜甜的忧愁”,至于诗人那点温柔的感觉,那点与日本女郎相同的“蜜甜的忧愁”是不是“爱情”,对我们又有什么重要呢?只要我们重视对诗的语言的实际感受和理解,我们就会感到,“爱情”这个词对于这首诗太大、太重、太严肃了.
总之,文学的语言是有质感的语言 是可以用心灵触摸的语言,是可以摸到硬度、掂出重量、看到颜色的语言.语文教学要不断加强学生对我们民族语言的这种质感的感觉,学生感受、理解和运用我们民族语言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我们民族语言的质感感觉的能力的提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