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定义是什么?我是一个农民,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神马作文网作业帮 分类:语文作业 时间:2024/11/19 07:17:49
农民的定义是什么?
我是一个农民,
我是一个农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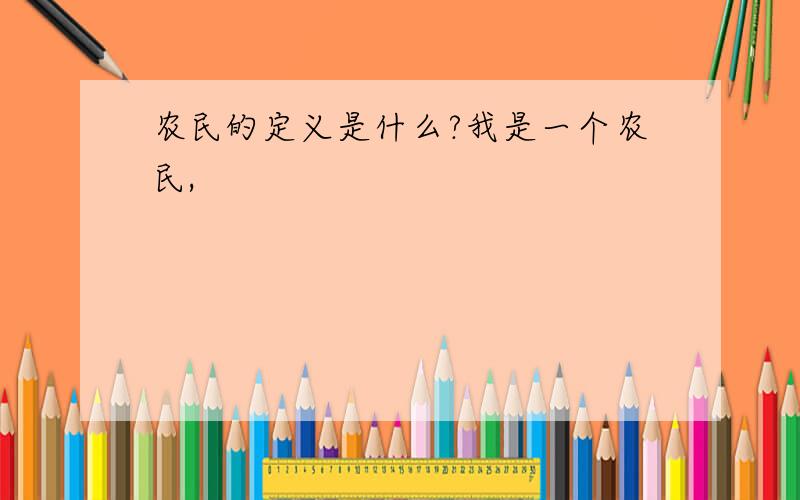
农民”与“农业者”
本刊前年推荐过麦天枢的电视系列片《中国农民》,该片一开场就提出了“什么是‘中国农民’”的问题,片中的被问者之回答人言各殊,莫衷一是,颇耐人寻味.
其实何止“中国”农民,外国农民亦然;何止社会各界,农民研究的专家亦然.著名英国人类学家M·布洛克曾说:学术界“在议论究竟什么是农民时面临巨大困难”.国际上权威的工具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农民(Peasants)”词条也困惑地写道:“很少有哪个名词像‘农民’这样给农村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造成这么多困难.什么是‘农民’?即便在地域上只限于西欧,时间上只限于过去1000年内,这一定义仍是个问题.”西方学术界从60年代以来就兴起了“农民”定义问题的论战.到70年代中期正如德国学者欣德尔抱怨的:“关于如何定义‘农民’的论战已经拖得太久了,以至于不少人认为继续这种讨论纯属浪费时间与精力.”但他也看到:“这一论战事关农民研究的未来,因此讨论仍将继续下去.”一直到90年代,“谁是‘农民’”似乎仍是个问题,以至于英国农民学家T.沙宁在1990年出版的一本颇有影响的书便以《定义中的农民》为题.
“农民”不就是以农为生的种田人吗?的确,在当代发达国家,农民(farmer)完全是个职业概念,指的就是经营farm(农场、农业)的人.这个概念与fisher(渔民)、artisan(工匠)、merchant(商人)等职业并列.而所有这些职业的就业者都具有同样的公民(citzen)权利,亦即在法律上他们都是市民(西语中公民、市民为同一词),只不过从事的职业有别.这样的“农民(farmer)”不存在定义问题:务农者即为farmer,一旦不再务农也就不复为farmer了,但无论务农与否,他与“市民”之间并无身份等级界限.
然而在许多不发达社会,农民一般不被称为farmer而被视作peasant.而peasant(汉语“农民”的主要对应词)的定义则远比farmer为复杂.无论在研究中还是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人们谈到“农民”时想到的都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而且一般说来,社会越不发达,后面这些涵义就越显得比“农民”一词的职业涵义重要.在这些社会里,不仅种田人是“农民”,就是许多早已不种田的人、住在城里的人,也被认为具有“农民”身份.如本世纪初英属印度的孟加拉地区,绝大多数下层的非农职业人口都自认为、也被认为仍属于“农民”,因为他们不仅都是种田人的兄弟或儿孙,而且他们的“家内习惯与生活准则”也与农民无异.调查还表明:当地农民自己对“什么是农民”的回答也更多地与地位而不是与职业相联系的.
在这点上,我们中国人应当深有体会.例如:如今在城里谋生的所谓“农民工”中,有1/3以上(有些调查甚至说是半数以上)实际上是走出校门便进城闯世界的乡村青年,他们中很多人连一天农活也没干过,然而别人和他们自己都把他们看成“打工的农民”.相反,笔者15岁以后曾在农村插队务农9年多,但不仅现在不会有人称笔者为“农民教师”(如称“农民工”那样),就是在当年,“知青”与“农民”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两个概念.事实上,如今的“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与“离土不离乡”等现象都与“农民”改了业却改不了“身份”这一事实有着逻辑联系.
因此,在国际上关于农民定义的讨论中,Peasant与farmer的区别是常被提到的.但这两个英文词一般都译作“农民”,这就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例如国外有不少论述“from?peasants?to?farmers”过程的论著,若把这一过程译作“从农民到农民”就会让人不知所云.因此我国学术界有人译作“从贫苦农民到现代农民”,也有人译作“从农民到农场主”,实际上都不很贴切.而我们这本《中国农民》杂志的英译名也是个问题:译作Chinese?Peasantry吧容易使人得到中国农民仍是传统的贱民身份的印象,译作Chinese?Farmers吧又难以反映本刊对象中包括大量从事非农业的“农民”这一现实.
但根本的问题还不在于翻译,而在于作为公民自由职业的农民(farmer)与作为传统身份等级的农民(peasant)之区别是客观存在的.笔者建议参照“工商业者”、“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之类称呼,把farmer译作“农业者”.显然,我国“农民”目前仍然主要是一个身份概念而不是一个职业概念.“从农民到农业者”的演进在我国远未完成,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农民身份者,这一事实比我国有大量人口实际上在田间劳作一事更深刻地体现了我国目前的不发达状态.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后一事实意味着产业上的不发达,那么前一事实则意味着社会的不发达.而身份性“农民”比重之庞大远远超过实际务农者的比重,则说明我国社会的发展已经明显滞后于产业的发展.
农民(peasant)与农业者(farmer)的区别何在?从词义上说,farmer以farm(农业)为词根,强调的是职业涵义;而peasant一词从词源及构词成分看与“农业”、种田等本无直接关系.该词源于古法语,系由古拉丁语pagus派生,该拉丁词意为“异教徒、未开化者、堕落者”,带有强烈的贬义,因而peasant在古代的本义是对卑贱者的贬称.在古英语中Peasant可作动词用,意为“附庸、奴役”,而作名词时还兼有“流氓”、“坏蛋”之意.因而它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种低下的身份或出身.只是由于那时卑贱者大多种田,这个词后来才与农业有了关系. 不仅英、法、拉丁语如此,俄语、波兰语等欧洲语言中近代表示农民的词汇也有类似特点:原无带有“农”义的构词成分,只是泛指卑贱者或依附者而言.古汉语中“农民”一词始见于战国时也有身份的涵义(《说文》释民:“萌(懵)而无识也.”),但并无西方语言那样强烈,而职业涵义(繁体“农”字从辰,古指贝壳制的农具)却很明显.“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春秋谷梁传》).从这类表述看,古代中国“农民”这一概念比西方有更多的职业涵义,而身份卑贱之义却较为淡化.这反映了古代中国比当时的西方职业分化较明显而身份壁垒却较宽疏,这无疑是当时中国比西方更进步、更文明的体现.遗憾的是到了本世纪中叶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社会的身份性色彩反而空前地增浓了.直到改革时代,这种状况才逐渐改变. 身份性农民与自然经济(或西方经济学家所谓的“习俗指令经济”)相联系,而农业者则与市场经济相联系.E·R·沃尔夫的说法在国外学者中颇有代表性:“农民的主要追求在于维持生计,并在一个社会关系的狭隘等级系列中维持其社会身份.因此农民就不像那些专门为满足市场而生产、并使自己在一个广泛的社会网络内置身于地位竞争之中的耕作者”,因为他必须“固守传统安排”.“相反地,农业者则充分地进入市场,使自己的土地与劳动从属于开放的竞争,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以使报酬极大化,并倾向于在更小的风险基础上进行可获更大利润的生产.” 这种说法与我们过去常说的自然经济中的传统农民与现代化农场之别有些类似.但须指出:当代西方学界对市场经济之前的传统经济的看法不同于过去的“自然经济”说.“自然经济”说强调“小生产”的自给自足和无交往,而现在人们则强调传统经济中交往的非市场性或曰强制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希克斯认为真正无交往无分工的“自给自足”可能并不存在,传统经济中可能有相当规模的分工与要素流动,只是它并非因市场而起,而是“典型官僚政治中”“由上层指导的专门化”.他把这称之为“习俗经济”与“指令经济”的结合.与此相应地,“自然经济说”强调传统的“小”生产与现代“大”生产之别,而“习俗指令经济”说则突出传统生产的不自由与现代生产的自主性.因此,是否“受外部权势支配”便成了传统农民不仅区别于现代农业者、也区别于比农民更古老的初民(primitives)或部落民(tribalpopulation)的主要标志.“人们已习惯于把服从上层国家专制的乡村人口与生活在这种政治结构之外的乡村居民对立起来,并以此区分农民与初民:前者是农民,而后者不是.”80年代新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农民”辞条正是基于这一点给“农民”下定义的.它认为在农民的定义中“诸如自给自足或小规模生产等特征”都未必成立,关键在于农民(peasant)“要受外部权势的支配”.这种“使其整合于更大社会的方式”才是农民与其他农业生产者的根本区别:“在农民社会,生产手段的最终支配权通常不是掌握在主要生产者手里.生产品及劳务不是由生产者直接交换,而是被提供给一些中心,重新分配.剩余的东西要转移到统治者和其他非农业者(non-farmers)手里.……这种权力往往集中于一个城市中心,尽管并非永远如此.”
显然,是用这样的观点还是用以往“自然经济说”的观点看待“从农民到农业者”的演进,结论会大不一样:按后一观点,斯大林式的集体农庄由于消灭了“小生产”,便可以说完成了“农民的改造”.但按前一观点,由于它强化了“外部权势的支配”,所以它在消灭了农业者的同时反倒强化了“农民社会”.按后一观点,我国改革后农村家庭经济的兴起是“乡土中国的重建”,而按前一观点,由于这种家庭农场具有市场基础而不再受“外部权势的支配”,所以它反而标志着“农民的终结”.
本刊前年推荐过麦天枢的电视系列片《中国农民》,该片一开场就提出了“什么是‘中国农民’”的问题,片中的被问者之回答人言各殊,莫衷一是,颇耐人寻味.
其实何止“中国”农民,外国农民亦然;何止社会各界,农民研究的专家亦然.著名英国人类学家M·布洛克曾说:学术界“在议论究竟什么是农民时面临巨大困难”.国际上权威的工具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农民(Peasants)”词条也困惑地写道:“很少有哪个名词像‘农民’这样给农村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造成这么多困难.什么是‘农民’?即便在地域上只限于西欧,时间上只限于过去1000年内,这一定义仍是个问题.”西方学术界从60年代以来就兴起了“农民”定义问题的论战.到70年代中期正如德国学者欣德尔抱怨的:“关于如何定义‘农民’的论战已经拖得太久了,以至于不少人认为继续这种讨论纯属浪费时间与精力.”但他也看到:“这一论战事关农民研究的未来,因此讨论仍将继续下去.”一直到90年代,“谁是‘农民’”似乎仍是个问题,以至于英国农民学家T.沙宁在1990年出版的一本颇有影响的书便以《定义中的农民》为题.
“农民”不就是以农为生的种田人吗?的确,在当代发达国家,农民(farmer)完全是个职业概念,指的就是经营farm(农场、农业)的人.这个概念与fisher(渔民)、artisan(工匠)、merchant(商人)等职业并列.而所有这些职业的就业者都具有同样的公民(citzen)权利,亦即在法律上他们都是市民(西语中公民、市民为同一词),只不过从事的职业有别.这样的“农民(farmer)”不存在定义问题:务农者即为farmer,一旦不再务农也就不复为farmer了,但无论务农与否,他与“市民”之间并无身份等级界限.
然而在许多不发达社会,农民一般不被称为farmer而被视作peasant.而peasant(汉语“农民”的主要对应词)的定义则远比farmer为复杂.无论在研究中还是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人们谈到“农民”时想到的都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而且一般说来,社会越不发达,后面这些涵义就越显得比“农民”一词的职业涵义重要.在这些社会里,不仅种田人是“农民”,就是许多早已不种田的人、住在城里的人,也被认为具有“农民”身份.如本世纪初英属印度的孟加拉地区,绝大多数下层的非农职业人口都自认为、也被认为仍属于“农民”,因为他们不仅都是种田人的兄弟或儿孙,而且他们的“家内习惯与生活准则”也与农民无异.调查还表明:当地农民自己对“什么是农民”的回答也更多地与地位而不是与职业相联系的.
在这点上,我们中国人应当深有体会.例如:如今在城里谋生的所谓“农民工”中,有1/3以上(有些调查甚至说是半数以上)实际上是走出校门便进城闯世界的乡村青年,他们中很多人连一天农活也没干过,然而别人和他们自己都把他们看成“打工的农民”.相反,笔者15岁以后曾在农村插队务农9年多,但不仅现在不会有人称笔者为“农民教师”(如称“农民工”那样),就是在当年,“知青”与“农民”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两个概念.事实上,如今的“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与“离土不离乡”等现象都与“农民”改了业却改不了“身份”这一事实有着逻辑联系.
因此,在国际上关于农民定义的讨论中,Peasant与farmer的区别是常被提到的.但这两个英文词一般都译作“农民”,这就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例如国外有不少论述“from?peasants?to?farmers”过程的论著,若把这一过程译作“从农民到农民”就会让人不知所云.因此我国学术界有人译作“从贫苦农民到现代农民”,也有人译作“从农民到农场主”,实际上都不很贴切.而我们这本《中国农民》杂志的英译名也是个问题:译作Chinese?Peasantry吧容易使人得到中国农民仍是传统的贱民身份的印象,译作Chinese?Farmers吧又难以反映本刊对象中包括大量从事非农业的“农民”这一现实.
但根本的问题还不在于翻译,而在于作为公民自由职业的农民(farmer)与作为传统身份等级的农民(peasant)之区别是客观存在的.笔者建议参照“工商业者”、“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之类称呼,把farmer译作“农业者”.显然,我国“农民”目前仍然主要是一个身份概念而不是一个职业概念.“从农民到农业者”的演进在我国远未完成,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农民身份者,这一事实比我国有大量人口实际上在田间劳作一事更深刻地体现了我国目前的不发达状态.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后一事实意味着产业上的不发达,那么前一事实则意味着社会的不发达.而身份性“农民”比重之庞大远远超过实际务农者的比重,则说明我国社会的发展已经明显滞后于产业的发展.
农民(peasant)与农业者(farmer)的区别何在?从词义上说,farmer以farm(农业)为词根,强调的是职业涵义;而peasant一词从词源及构词成分看与“农业”、种田等本无直接关系.该词源于古法语,系由古拉丁语pagus派生,该拉丁词意为“异教徒、未开化者、堕落者”,带有强烈的贬义,因而peasant在古代的本义是对卑贱者的贬称.在古英语中Peasant可作动词用,意为“附庸、奴役”,而作名词时还兼有“流氓”、“坏蛋”之意.因而它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种低下的身份或出身.只是由于那时卑贱者大多种田,这个词后来才与农业有了关系. 不仅英、法、拉丁语如此,俄语、波兰语等欧洲语言中近代表示农民的词汇也有类似特点:原无带有“农”义的构词成分,只是泛指卑贱者或依附者而言.古汉语中“农民”一词始见于战国时也有身份的涵义(《说文》释民:“萌(懵)而无识也.”),但并无西方语言那样强烈,而职业涵义(繁体“农”字从辰,古指贝壳制的农具)却很明显.“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春秋谷梁传》).从这类表述看,古代中国“农民”这一概念比西方有更多的职业涵义,而身份卑贱之义却较为淡化.这反映了古代中国比当时的西方职业分化较明显而身份壁垒却较宽疏,这无疑是当时中国比西方更进步、更文明的体现.遗憾的是到了本世纪中叶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社会的身份性色彩反而空前地增浓了.直到改革时代,这种状况才逐渐改变. 身份性农民与自然经济(或西方经济学家所谓的“习俗指令经济”)相联系,而农业者则与市场经济相联系.E·R·沃尔夫的说法在国外学者中颇有代表性:“农民的主要追求在于维持生计,并在一个社会关系的狭隘等级系列中维持其社会身份.因此农民就不像那些专门为满足市场而生产、并使自己在一个广泛的社会网络内置身于地位竞争之中的耕作者”,因为他必须“固守传统安排”.“相反地,农业者则充分地进入市场,使自己的土地与劳动从属于开放的竞争,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以使报酬极大化,并倾向于在更小的风险基础上进行可获更大利润的生产.” 这种说法与我们过去常说的自然经济中的传统农民与现代化农场之别有些类似.但须指出:当代西方学界对市场经济之前的传统经济的看法不同于过去的“自然经济”说.“自然经济”说强调“小生产”的自给自足和无交往,而现在人们则强调传统经济中交往的非市场性或曰强制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希克斯认为真正无交往无分工的“自给自足”可能并不存在,传统经济中可能有相当规模的分工与要素流动,只是它并非因市场而起,而是“典型官僚政治中”“由上层指导的专门化”.他把这称之为“习俗经济”与“指令经济”的结合.与此相应地,“自然经济说”强调传统的“小”生产与现代“大”生产之别,而“习俗指令经济”说则突出传统生产的不自由与现代生产的自主性.因此,是否“受外部权势支配”便成了传统农民不仅区别于现代农业者、也区别于比农民更古老的初民(primitives)或部落民(tribalpopulation)的主要标志.“人们已习惯于把服从上层国家专制的乡村人口与生活在这种政治结构之外的乡村居民对立起来,并以此区分农民与初民:前者是农民,而后者不是.”80年代新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农民”辞条正是基于这一点给“农民”下定义的.它认为在农民的定义中“诸如自给自足或小规模生产等特征”都未必成立,关键在于农民(peasant)“要受外部权势的支配”.这种“使其整合于更大社会的方式”才是农民与其他农业生产者的根本区别:“在农民社会,生产手段的最终支配权通常不是掌握在主要生产者手里.生产品及劳务不是由生产者直接交换,而是被提供给一些中心,重新分配.剩余的东西要转移到统治者和其他非农业者(non-farmers)手里.……这种权力往往集中于一个城市中心,尽管并非永远如此.”
显然,是用这样的观点还是用以往“自然经济说”的观点看待“从农民到农业者”的演进,结论会大不一样:按后一观点,斯大林式的集体农庄由于消灭了“小生产”,便可以说完成了“农民的改造”.但按前一观点,由于它强化了“外部权势的支配”,所以它在消灭了农业者的同时反倒强化了“农民社会”.按后一观点,我国改革后农村家庭经济的兴起是“乡土中国的重建”,而按前一观点,由于这种家庭农场具有市场基础而不再受“外部权势的支配”,所以它反而标志着“农民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