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宋江起义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神马作文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11/14 14:43:38
如何看待宋江起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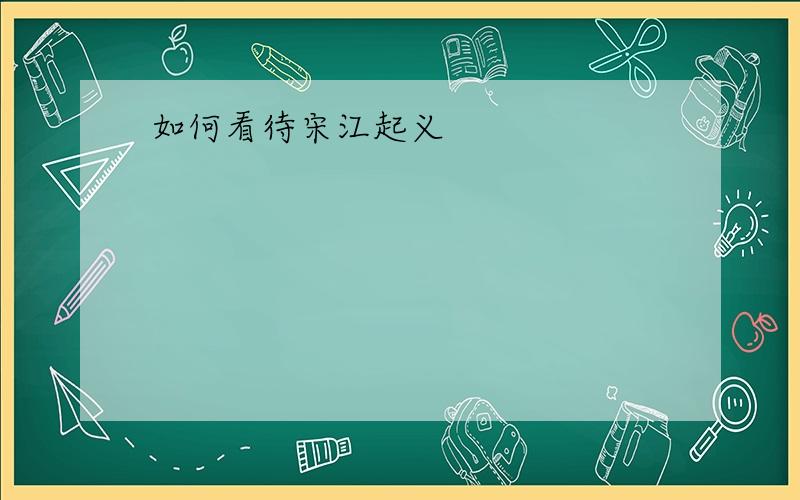
作者:王前程
近些年来,学术界不少学者对《水浒传》所歌颂的梁山好汉形象提出了质疑,如海外汉学家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里说,梁山好汉“先后有组织有系统地平毁了与梁山作对的祝家庄和曾头市,这只能说明他们的暴虐和贪婪”[1](P101),又说:“官府的不义不公,激发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反抗;而众好汉结成的群体却又损害了这种英雄主义,它制造了比腐败官府更为可怕的邪恶与恐怖统治”[1](P102).大陆学者陈洪、孙勇进二位先生合著的《漫说水浒》在夏志清教授的基础上进一步清理了梁山好汉野蛮暴戾的行为,在指责了武松的血溅鸳鸯楼、宋江的计逼秦明入伙、李逵的劈杀小衙内、吴用的烧杀北京城等事件之后不无感慨地说:“水浒世界里的很多血腥气冲鼻的行为,连追求正义的幌子都没有,完全是为蛮荒的嗜血心理所驱使”[2](P54),“因此,在下对这‘替天行道’,卑之无甚高论”[2](P32).陈、孙二位先生最后总结道:“正如夏志清先生所分析的那样:‘尽管司马迁对吕后残害行为的描写颇为客观,但当他写到吕后的儿子的强烈的反感时,已对吕后做了永久的判决.《史记》肯定文明事业;而《水浒》在对英雄们采取的野蛮报复行为大加赞赏之时,却并不是肯定文明.’……一部《水浒》中,值得我们深刻反省的内容是太多太多了”[2](P52).
如何评价《水浒传》?如何看待梁山好汉的暴力行为?这其实是个明清以来就争论不休的老话题.明清学界“忠义”说与“诲盗”说相互对立,所谓“盗”者,即为非作歹的盗匪也.主张理性地分辨《水浒》人物的思想行为是完全正确的,但指责梁山好汉的所作所为类同暴虐的恐怖分子,比腐败官府、滥官污吏更可怕,这同明清时期封建官僚和正统文人指责《水浒》歌颂了一群杀人放火的强盗的论调即“诲盗”说岂非如出一辙?难道《水浒传》真的否定了文明、歌颂了暴力行为?梁山世界的“替天行道”真的不值得一提吗?诚然,梁山好汉集团确实存在着乱杀乱砍、残害生灵的暴力行为,这种行为在任何时代都应受到毫不留情的抨击,但不能因此否认整个梁山集团与梁山事业的正义性,不能否认小说思想内容的进步性.这主要有四条理由:
一、正义集团、仁义之师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出现乱杀乱砍现象是在所难免的
任何进步的团体、政党或正义力量都要经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必然过程,在草创时期,由于缺乏必要的集体约束力及计划的周密性,因此在行动中往往会发生任意胡为殃及无辜的事情.比如,《水浒》写武松血溅鸳鸯楼、李逵江州乱杀乱砍等皆是缺乏集体约束力、任凭个体英雄复仇火焰燃烧的结果,而吴用攻打大名府殃及无辜百姓则是攻城时没有采取得力措施做周密安排所致,后来在多次攻城略地的军事行动中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事实上,乱杀乱砍现象随着梁山义军的成长而逐渐减少,在一百零八好汉聚义梁山之前,乱杀无辜、残害生命的事件有7、8次,聚义之后仅有2次,而且伤害无辜的程度不大.宋江多次告诫手下,要“改邪归正”、“弃邪归正”,虽然是号召好汉们走出山林接受朝廷招安,但也包含了要求好汉们抛弃乱杀无辜危害生灵之恶习的意思,这正说明梁山英雄对理想、光明和正义的追求.二十世纪先进的共产党军队在草创之初也时有过分烧杀、虐待俘虏及逃兵之类的现象,后来逐步完善成为真正的仁义之师,其先进性和完美性当然不是梁山好汉所能比,但是,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八九百年前的英雄豪杰,否则,古代无正义光明可言.
二、梁山好汉的暴力倾向是封建时代险恶环境的产物
应当承认,《水浒传》塑造的好汉都充满“匪气”,好汉们动辄放泼撒野,甚至杀人放火.然而,小说是在历史传说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审视梁山好汉的思想行为自然不能脱离作品所提供的历史背景.梁山故事发生在北宋末年的徽宗时期,小说深刻地展示了这一时期的严酷现实:朝政窳败,是非颠倒,“赃吏纷纷据要津”,“狼心狗幸滥居官”,以致盗贼蜂起,外敌凭陵,天下失控,国势飘摇.这是个典型的奸邪当道、小人得志而君子困顿、英雄失路的悲剧时代.生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如何去适应严酷的现实环境呢?当我们把注意力停留在梁山好汉的暴力行为上的时候,也许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梁山世界为什么存在暴力倾向,与这个社会是否有关联?
小说第52回写柴进幻想利用法律条文向当权者讨回公道,而李逵大声嚷道:“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这句话的重大价值在于它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封建社会生存环境的恶劣,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法律不仅不能维护公道,反而成了邪恶小人手中随意残害忠良的工具.在《水浒传》里,邪恶的统治者贪赃枉法,胡作非为,百姓哭告无门,大批忠良贤士横遭迫害,作品一再写到监牢中犯人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的场面,这正是统治阶级动辄用严刑峻法打击异己、迫害弱小百姓的写照.在此险恶环境下,正直的人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任凭摧残被赶尽杀绝,要么做强人用暴力回报暴力.这个社会本来就是一个以上欺下以强凌弱、缺乏温情不讲文明的黑暗专制社会,梁山好汉习惯凭借自己的双拳主持公道,热中使用暴力解决问题,“匪气”十足,这不正是公道不存的黑暗专制社会的产物吗?作者在第38回曾赋诗道:“贿赂公行法枉施,罪人多受不平亏.以强凌弱真堪恨,天使拳头付李逵.”明确告诉世人,梁山好汉的粗野嗜杀是邪恶的统治者逼良为盗的结果,连上天也理解支持他们的“匪气”.所以,任何时代的读者读《水浒传》都应该从这个角度切入.清人王韬说得好:“试观一百八人中,谁是甘心为盗者?必至于穷途势迫,甚不得已,无可如何,乃出于此.盖于时,宋室不纲,政以贿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赏善罚恶,倒持其柄.贤人才士,困踣流离,至无地以容身.其上者隐遁以自全,其下者遂至失身于盗贼.呜呼!谁使之然?当轴者固不得不任其咎.能以此意读《水浒传》,方谓善读《水浒传》者也”[3](P45).
三、梁山世界并非没有是非观念,“替天行道”决不是一块大而空的招牌
陈洪、孙勇进等先生认为,梁山世界推崇江湖行帮道德,好汉们奉行的人生价值信条是江湖黑道的快意恩仇,而“快意恩仇,说到底,是全然以一己之恩怨为是非标准.有恩报恩,哪怕这恩人是个恶棍;有仇报仇,哪怕其曲在己,并且不惜滥杀无辜.而理性和良知,从来就是完全缺席的”[2](P30).梁山世界属于江湖绿林世界,好汉中不少人恩仇思想浓厚,为了报仇雪恨,或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常常采用江湖惯用的方式行事,滥杀无辜的现象时有发生.但梁山世界决不是以强欺弱、谋财害命的江湖黑道组织,梁山好汉决不是毫无理性和良知的黑道歹徒.
我们不妨举两个例子略作说明.一个例子是武松.这个被陈、孙二先生认为是水浒世界中最能体现“快意恩仇精神”的好汉其实并不胡来,为报杀兄之仇,他只杀了主谋西门庆和潘金莲,并没有伤害那些冷木的街坊邻居;他替施恩打蒋门神,不仅仅因为施恩关照了他,还因为蒋门神是强取豪夺的强徒;他在十字坡不让孙二娘毒杀两个护送公人,是因为这两个公人忠厚本分,“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在蜈蚣岭,他斗杀了谋害人命强占妇女的奸恶道人,却让妇人携带钱财自去“养身”.惟独在鸳鸯楼,他除了杀死张都监、蒋门神等恶人外,还杀了不少奴仆.这里恐怕是两个因素所致:一是不杀这些撞见的人就不能顺利脱身逃走,二是他认为养娘玉兰之类的仆妇参与了张都监的阴谋,不杀难平心头之恨.可见,理性和良知在武松的灵魂深处并未完全缺席.另一个例子是梁山好汉捕杀黄文炳.宋江因黄文炳的调唆而吃尽了牢狱之苦,险些丧命,在被众好汉搭救后主动提出捕杀仇人黄文炳的要求,但听说黄文炳有个嫡亲兄长叫黄文烨,此人“平生只是行善事,修桥补路,塑佛斋僧,扶危济困,救拔贫苦,那无为军城中都叫他黄佛子”,因而宋江吩咐众好汉道:“只恨黄文炳那贼一个,却与无为军百姓无干.他兄既然仁德,亦不可害他.休教天下人骂我等不仁.众弟兄去时,不可分毫侵害百姓.”足见梁山世界有着鲜明的是非观念和惩恶扬善的处世原则.正是这鲜明的是非观和心头长存的理性原则,使得梁山好汉集团与自私卑劣、歹毒残忍的黑道邪恶势力迥然有别.这一点夏志清先生也坦率承认:“对初读这部小说的读者来说,这些动辄实行暴力的英雄有时候几乎同歹徒难以区分.但好汉毕竟同歹徒是泾渭分明的”[1](P92),“菜园子张青和妻子开了爿黑店,以杀害顾客、掠其钱财为业.但他们都有资格作为好汉社会中的成员,因为他们从不谋杀处于社会下层的流犯、僧人、娼优之类人物”[1](P93).
的确,在《水浒》作者的笔下,梁山好汉不是横行江湖黑道的匪徒,而是被腐败官府逼入江湖绿林的忠良之士,是黑暗时代代表正义光明的英雄人物.小说写梁山之上飘扬着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黄旗,这面旗帜标明了梁山好汉集团的宏大志向和正义性.所谓“替天行道”就是替上天或朝廷主持公道,为百姓伸张正义.陈洪、孙勇进二位先生否认梁山好汉信守替天行道之大义:“纯出于大济苍生、替天行道的理想主义动机而上山的,可以说一个也没有”[2](P38).梁山好汉中多数人来自社会基层,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头脑中的确很难说装着高尚的大济苍生的理想主义,但在一个君昏臣乱、政治腐败、公道不彰的黑暗社会里,他们奉行一套惩恶锄强、扶危济困的侠义原则,虽然这样做并不能从根本上拯救苦难中的民众,但多少能为苦难的民众带来一线生存的希望,这难道不属于替天行道、大济苍生的范畴?
事实上,梁山好汉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和民众的事情,“替天行道”决不是一块大而空的招牌.如鲁智深、史进、武松等人的惩恶扬善,宋江、柴进等人的周济贫困,而梁山武装集团惩办的官员几乎无一不是为非作歹的贪官污吏,如梁中书、贺太守、张都监、刘知寨、高廉等等.小说第71回介绍说:“泊子里好汉,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财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挡!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足见梁山世界扶弱锄强的侠义肝胆.在小说中,梁山义军还处处以吊民伐罪的正义之师出现,“所过州县,秋毫无犯”之类的词语出现了13次,“不害良民”、“不掠良民”、“休得伤害百姓”之类的词语出现了11次.当外敌凭陵、民族危难之时,他们挺身而出,开赴狼烟未熄的边关,担负起保国安民的神圣使命.显然,在作家心目中,以宋江为首的一百八人是乱世英雄,他们在那个公道不存、风雨飘摇的时代里高高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为苦难的人民和衰弱的民族点燃正义、希望之火.所以,任何时代的读者不能因为梁山英雄有过残忍伤害无辜者的事件,就否认其主流的正义性,否认其替天行道的高尚性.明人余象斗早就批驳过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味夸大水浒世界的暴力行为而看不到梁山好汉仗义行善的君子风范的偏见:“当是时,宋德衰微,乾纲不揽,官箴失措,下民咨咨,山谷嗷嗷,英雄豪杰,愤国治之不平,悯民庶之失所,乃崛起山东…….不知者曰:此民之贼也,国之蠹也.噫!不然也,彼盖强者锄之,弱者扶之,富者削之,贫者周之,冤屈者起而伸之,囚困者斧而出之,原其心未必为仁者博施济众,按其行事之迹,可谓桓文仗义,并轨君子”[3](P9).
四、小说渲染血腥场景是取悦听众和读者的结果,但作者并不赞成乱杀无辜
《水浒传》大量描写和渲染暴力行为是客观存在的倾向,出现这种倾向除了小说选择的特殊题材这个因素外,还同都市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宋元时期,随着都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日益壮大,产生了迎合市民阶层审美心理和口味的都市文化.都市文化的基本特征是讲究消闲娱乐,追逐新奇热闹,寻求感官刺激.水浒故事最初正是流行于都市文化高度发展的宋元时期,为了取悦都市听众,说书艺人们(即《水浒》的早期作者)挖掘一些新奇热闹的内容、渲染一些刺激感官的场景以取得消闲娱乐的效果,正如今天的影视界为了吸引观众而乐意拍摄荒诞喜剧片和暴力色情片一样.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李逵形象的塑造,陈洪、孙勇进二位先生认为李逵是《水浒》中最嗜血最野蛮最残暴的人,然而,李逵的身上喜剧搞笑的娱乐成分明显多于严肃的成分.李逵在江州酒楼一指头点晕卖唱女子,见卖唱女子“额角上抹脱了一片油皮”,便道:“不曾见这般鸟女子,恁地娇嫩!你便在我脸上打一百拳也不妨!”你能把这看作是李逵的凶狠残暴吗?李逵在寿张县穿着绿袍公服闯进学堂,丑陋而狰狞的样子吓得先生跳窗而逃,吓得学生们“哭的哭,叫的叫,跑的跑,躲的躲.”我们与其将这理解为制造恐怖,还不如理解为制造笑料.李逵在狄家庄冒充法师捉鬼,骗了许多酒肉狂吃暴饮,然后闯进房里一斧砍杀了一对装神弄鬼的偷情者,并在死尸上乱剁一阵,笑道:“眼见这两个不得活了.”说书艺人在此处的主要意图还是制造笑料,只是有些过头了.即使是一些重大严肃事件的描写也仍然带有娱乐消遣的意味.如打破祝家庄后李逵闯入扈家庄,赶走扈成,杀尽扈三娘一家老小,回来后遭到宋江训斥,李逵叫道:“你便忘记了,我须不忘记!那厮前日教那个鸟婆娘赶着哥哥要杀,你今却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亲,便又思量阿舅、丈人.”此类取悦听众的笑料的穿插大大降低了事件的严肃性和真实性,换句话说,作品中许多暴力行为和暴力场景的描写带有明显的虚构和夸饰成分,其目的是为了迎合都市听众和读者的审美心理,而大多数听众和读者也只是把这看作演戏,消遣,好玩,未必真的拿它当一回事,所以,我们不必过于认真计较.诚然,这种为取悦观众而渲染暴力的做法,影响是消极的,今天的人们无疑应该抛弃这种不良倾向.
追求娱乐消闲的都市文化对《水浒传》的确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我不赞同夏志清、陈洪、孙勇进等先生的看法———小说肯定暴力而否定文明.尽管《水浒》的作者是由不同时期的艺人、文人组成,思想倾向比较复杂,但基本态度是一致的,即反对乱杀无辜,反对残害良民.比如宋江计赚秦明入伙和李逵劈杀小衙内两个事件,这两件事确实表现了江湖黑道的恶习:为达到目的而不惜乱杀无辜.然而,作者显然是不赞成这种歹毒的做法的,他写秦明“怒气于心”,“说道:‘你们弟兄虽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个.’”又让朱仝说道:“是则是你们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个!”这里无疑包含着对好汉集团乱杀无辜的暴力行为的批评.而对残害百姓的行为作者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第40回写江州劫法场,无人约束的李逵“不问官军百姓”,“排头儿砍将去”.作者让晁盖大声喊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第66回写梁山人马攻打大名府,虽然事前做过周密的安排,遍贴布告,晓谕城中居民不要随意外出,但在攻城之日却又未采取得力措施保护城中居民,导致一片混乱.作者写蔡福对柴进说:“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残害”.可是,“比及柴进寻着吴用,急传下号令去,休教杀害良民时,城中将及伤损一半.”作者不袒护梁山英雄,对他们在军事行动中造成贫民百姓的伤亡深表遗憾和不满.这些情节充分表现了作者爱护百姓、反对非正义的暴力行为的鲜明立场,怎么能说《水浒传》没有肯定文明?怎么能说“中国小说在对待正义的态度上含糊不清、对地道的暴力像孩子似的津津乐道”?[1](P109~110)
至于作者称赞梁山英雄平毁祝家庄和曾头市,能不能说小说肯定了“暴虐和贪婪”呢?我以为不能.平毁祝家庄和曾头市固然算不上真正的吊民伐罪之举,但祝家庄和曾头市站在官府黑暗势力一边,将梁山好汉集团视为反贼,发誓要“扫荡梁山清水泊”,活捉义军首领,赶尽杀绝,打掉这样的地主武装,谈不上暴虐蛮横.同时,梁山人马日益壮大,需要大量物资给养,寻找富有的地主庄园作为补给线,也说不上贪婪.
水浒世界匪气十足,但那是黑暗专制社会的造就;梁山英雄杀人放火,但决非杀人放火的恐怖匪徒所可同日而语;《水浒》作者渲染暴力场景,但并未葬送文明.
近些年来,学术界不少学者对《水浒传》所歌颂的梁山好汉形象提出了质疑,如海外汉学家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里说,梁山好汉“先后有组织有系统地平毁了与梁山作对的祝家庄和曾头市,这只能说明他们的暴虐和贪婪”[1](P101),又说:“官府的不义不公,激发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反抗;而众好汉结成的群体却又损害了这种英雄主义,它制造了比腐败官府更为可怕的邪恶与恐怖统治”[1](P102).大陆学者陈洪、孙勇进二位先生合著的《漫说水浒》在夏志清教授的基础上进一步清理了梁山好汉野蛮暴戾的行为,在指责了武松的血溅鸳鸯楼、宋江的计逼秦明入伙、李逵的劈杀小衙内、吴用的烧杀北京城等事件之后不无感慨地说:“水浒世界里的很多血腥气冲鼻的行为,连追求正义的幌子都没有,完全是为蛮荒的嗜血心理所驱使”[2](P54),“因此,在下对这‘替天行道’,卑之无甚高论”[2](P32).陈、孙二位先生最后总结道:“正如夏志清先生所分析的那样:‘尽管司马迁对吕后残害行为的描写颇为客观,但当他写到吕后的儿子的强烈的反感时,已对吕后做了永久的判决.《史记》肯定文明事业;而《水浒》在对英雄们采取的野蛮报复行为大加赞赏之时,却并不是肯定文明.’……一部《水浒》中,值得我们深刻反省的内容是太多太多了”[2](P52).
如何评价《水浒传》?如何看待梁山好汉的暴力行为?这其实是个明清以来就争论不休的老话题.明清学界“忠义”说与“诲盗”说相互对立,所谓“盗”者,即为非作歹的盗匪也.主张理性地分辨《水浒》人物的思想行为是完全正确的,但指责梁山好汉的所作所为类同暴虐的恐怖分子,比腐败官府、滥官污吏更可怕,这同明清时期封建官僚和正统文人指责《水浒》歌颂了一群杀人放火的强盗的论调即“诲盗”说岂非如出一辙?难道《水浒传》真的否定了文明、歌颂了暴力行为?梁山世界的“替天行道”真的不值得一提吗?诚然,梁山好汉集团确实存在着乱杀乱砍、残害生灵的暴力行为,这种行为在任何时代都应受到毫不留情的抨击,但不能因此否认整个梁山集团与梁山事业的正义性,不能否认小说思想内容的进步性.这主要有四条理由:
一、正义集团、仁义之师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出现乱杀乱砍现象是在所难免的
任何进步的团体、政党或正义力量都要经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必然过程,在草创时期,由于缺乏必要的集体约束力及计划的周密性,因此在行动中往往会发生任意胡为殃及无辜的事情.比如,《水浒》写武松血溅鸳鸯楼、李逵江州乱杀乱砍等皆是缺乏集体约束力、任凭个体英雄复仇火焰燃烧的结果,而吴用攻打大名府殃及无辜百姓则是攻城时没有采取得力措施做周密安排所致,后来在多次攻城略地的军事行动中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事实上,乱杀乱砍现象随着梁山义军的成长而逐渐减少,在一百零八好汉聚义梁山之前,乱杀无辜、残害生命的事件有7、8次,聚义之后仅有2次,而且伤害无辜的程度不大.宋江多次告诫手下,要“改邪归正”、“弃邪归正”,虽然是号召好汉们走出山林接受朝廷招安,但也包含了要求好汉们抛弃乱杀无辜危害生灵之恶习的意思,这正说明梁山英雄对理想、光明和正义的追求.二十世纪先进的共产党军队在草创之初也时有过分烧杀、虐待俘虏及逃兵之类的现象,后来逐步完善成为真正的仁义之师,其先进性和完美性当然不是梁山好汉所能比,但是,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八九百年前的英雄豪杰,否则,古代无正义光明可言.
二、梁山好汉的暴力倾向是封建时代险恶环境的产物
应当承认,《水浒传》塑造的好汉都充满“匪气”,好汉们动辄放泼撒野,甚至杀人放火.然而,小说是在历史传说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审视梁山好汉的思想行为自然不能脱离作品所提供的历史背景.梁山故事发生在北宋末年的徽宗时期,小说深刻地展示了这一时期的严酷现实:朝政窳败,是非颠倒,“赃吏纷纷据要津”,“狼心狗幸滥居官”,以致盗贼蜂起,外敌凭陵,天下失控,国势飘摇.这是个典型的奸邪当道、小人得志而君子困顿、英雄失路的悲剧时代.生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如何去适应严酷的现实环境呢?当我们把注意力停留在梁山好汉的暴力行为上的时候,也许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梁山世界为什么存在暴力倾向,与这个社会是否有关联?
小说第52回写柴进幻想利用法律条文向当权者讨回公道,而李逵大声嚷道:“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这句话的重大价值在于它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封建社会生存环境的恶劣,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法律不仅不能维护公道,反而成了邪恶小人手中随意残害忠良的工具.在《水浒传》里,邪恶的统治者贪赃枉法,胡作非为,百姓哭告无门,大批忠良贤士横遭迫害,作品一再写到监牢中犯人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的场面,这正是统治阶级动辄用严刑峻法打击异己、迫害弱小百姓的写照.在此险恶环境下,正直的人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任凭摧残被赶尽杀绝,要么做强人用暴力回报暴力.这个社会本来就是一个以上欺下以强凌弱、缺乏温情不讲文明的黑暗专制社会,梁山好汉习惯凭借自己的双拳主持公道,热中使用暴力解决问题,“匪气”十足,这不正是公道不存的黑暗专制社会的产物吗?作者在第38回曾赋诗道:“贿赂公行法枉施,罪人多受不平亏.以强凌弱真堪恨,天使拳头付李逵.”明确告诉世人,梁山好汉的粗野嗜杀是邪恶的统治者逼良为盗的结果,连上天也理解支持他们的“匪气”.所以,任何时代的读者读《水浒传》都应该从这个角度切入.清人王韬说得好:“试观一百八人中,谁是甘心为盗者?必至于穷途势迫,甚不得已,无可如何,乃出于此.盖于时,宋室不纲,政以贿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赏善罚恶,倒持其柄.贤人才士,困踣流离,至无地以容身.其上者隐遁以自全,其下者遂至失身于盗贼.呜呼!谁使之然?当轴者固不得不任其咎.能以此意读《水浒传》,方谓善读《水浒传》者也”[3](P45).
三、梁山世界并非没有是非观念,“替天行道”决不是一块大而空的招牌
陈洪、孙勇进等先生认为,梁山世界推崇江湖行帮道德,好汉们奉行的人生价值信条是江湖黑道的快意恩仇,而“快意恩仇,说到底,是全然以一己之恩怨为是非标准.有恩报恩,哪怕这恩人是个恶棍;有仇报仇,哪怕其曲在己,并且不惜滥杀无辜.而理性和良知,从来就是完全缺席的”[2](P30).梁山世界属于江湖绿林世界,好汉中不少人恩仇思想浓厚,为了报仇雪恨,或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常常采用江湖惯用的方式行事,滥杀无辜的现象时有发生.但梁山世界决不是以强欺弱、谋财害命的江湖黑道组织,梁山好汉决不是毫无理性和良知的黑道歹徒.
我们不妨举两个例子略作说明.一个例子是武松.这个被陈、孙二先生认为是水浒世界中最能体现“快意恩仇精神”的好汉其实并不胡来,为报杀兄之仇,他只杀了主谋西门庆和潘金莲,并没有伤害那些冷木的街坊邻居;他替施恩打蒋门神,不仅仅因为施恩关照了他,还因为蒋门神是强取豪夺的强徒;他在十字坡不让孙二娘毒杀两个护送公人,是因为这两个公人忠厚本分,“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在蜈蚣岭,他斗杀了谋害人命强占妇女的奸恶道人,却让妇人携带钱财自去“养身”.惟独在鸳鸯楼,他除了杀死张都监、蒋门神等恶人外,还杀了不少奴仆.这里恐怕是两个因素所致:一是不杀这些撞见的人就不能顺利脱身逃走,二是他认为养娘玉兰之类的仆妇参与了张都监的阴谋,不杀难平心头之恨.可见,理性和良知在武松的灵魂深处并未完全缺席.另一个例子是梁山好汉捕杀黄文炳.宋江因黄文炳的调唆而吃尽了牢狱之苦,险些丧命,在被众好汉搭救后主动提出捕杀仇人黄文炳的要求,但听说黄文炳有个嫡亲兄长叫黄文烨,此人“平生只是行善事,修桥补路,塑佛斋僧,扶危济困,救拔贫苦,那无为军城中都叫他黄佛子”,因而宋江吩咐众好汉道:“只恨黄文炳那贼一个,却与无为军百姓无干.他兄既然仁德,亦不可害他.休教天下人骂我等不仁.众弟兄去时,不可分毫侵害百姓.”足见梁山世界有着鲜明的是非观念和惩恶扬善的处世原则.正是这鲜明的是非观和心头长存的理性原则,使得梁山好汉集团与自私卑劣、歹毒残忍的黑道邪恶势力迥然有别.这一点夏志清先生也坦率承认:“对初读这部小说的读者来说,这些动辄实行暴力的英雄有时候几乎同歹徒难以区分.但好汉毕竟同歹徒是泾渭分明的”[1](P92),“菜园子张青和妻子开了爿黑店,以杀害顾客、掠其钱财为业.但他们都有资格作为好汉社会中的成员,因为他们从不谋杀处于社会下层的流犯、僧人、娼优之类人物”[1](P93).
的确,在《水浒》作者的笔下,梁山好汉不是横行江湖黑道的匪徒,而是被腐败官府逼入江湖绿林的忠良之士,是黑暗时代代表正义光明的英雄人物.小说写梁山之上飘扬着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黄旗,这面旗帜标明了梁山好汉集团的宏大志向和正义性.所谓“替天行道”就是替上天或朝廷主持公道,为百姓伸张正义.陈洪、孙勇进二位先生否认梁山好汉信守替天行道之大义:“纯出于大济苍生、替天行道的理想主义动机而上山的,可以说一个也没有”[2](P38).梁山好汉中多数人来自社会基层,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头脑中的确很难说装着高尚的大济苍生的理想主义,但在一个君昏臣乱、政治腐败、公道不彰的黑暗社会里,他们奉行一套惩恶锄强、扶危济困的侠义原则,虽然这样做并不能从根本上拯救苦难中的民众,但多少能为苦难的民众带来一线生存的希望,这难道不属于替天行道、大济苍生的范畴?
事实上,梁山好汉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和民众的事情,“替天行道”决不是一块大而空的招牌.如鲁智深、史进、武松等人的惩恶扬善,宋江、柴进等人的周济贫困,而梁山武装集团惩办的官员几乎无一不是为非作歹的贪官污吏,如梁中书、贺太守、张都监、刘知寨、高廉等等.小说第71回介绍说:“泊子里好汉,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财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挡!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足见梁山世界扶弱锄强的侠义肝胆.在小说中,梁山义军还处处以吊民伐罪的正义之师出现,“所过州县,秋毫无犯”之类的词语出现了13次,“不害良民”、“不掠良民”、“休得伤害百姓”之类的词语出现了11次.当外敌凭陵、民族危难之时,他们挺身而出,开赴狼烟未熄的边关,担负起保国安民的神圣使命.显然,在作家心目中,以宋江为首的一百八人是乱世英雄,他们在那个公道不存、风雨飘摇的时代里高高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为苦难的人民和衰弱的民族点燃正义、希望之火.所以,任何时代的读者不能因为梁山英雄有过残忍伤害无辜者的事件,就否认其主流的正义性,否认其替天行道的高尚性.明人余象斗早就批驳过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味夸大水浒世界的暴力行为而看不到梁山好汉仗义行善的君子风范的偏见:“当是时,宋德衰微,乾纲不揽,官箴失措,下民咨咨,山谷嗷嗷,英雄豪杰,愤国治之不平,悯民庶之失所,乃崛起山东…….不知者曰:此民之贼也,国之蠹也.噫!不然也,彼盖强者锄之,弱者扶之,富者削之,贫者周之,冤屈者起而伸之,囚困者斧而出之,原其心未必为仁者博施济众,按其行事之迹,可谓桓文仗义,并轨君子”[3](P9).
四、小说渲染血腥场景是取悦听众和读者的结果,但作者并不赞成乱杀无辜
《水浒传》大量描写和渲染暴力行为是客观存在的倾向,出现这种倾向除了小说选择的特殊题材这个因素外,还同都市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宋元时期,随着都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日益壮大,产生了迎合市民阶层审美心理和口味的都市文化.都市文化的基本特征是讲究消闲娱乐,追逐新奇热闹,寻求感官刺激.水浒故事最初正是流行于都市文化高度发展的宋元时期,为了取悦都市听众,说书艺人们(即《水浒》的早期作者)挖掘一些新奇热闹的内容、渲染一些刺激感官的场景以取得消闲娱乐的效果,正如今天的影视界为了吸引观众而乐意拍摄荒诞喜剧片和暴力色情片一样.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李逵形象的塑造,陈洪、孙勇进二位先生认为李逵是《水浒》中最嗜血最野蛮最残暴的人,然而,李逵的身上喜剧搞笑的娱乐成分明显多于严肃的成分.李逵在江州酒楼一指头点晕卖唱女子,见卖唱女子“额角上抹脱了一片油皮”,便道:“不曾见这般鸟女子,恁地娇嫩!你便在我脸上打一百拳也不妨!”你能把这看作是李逵的凶狠残暴吗?李逵在寿张县穿着绿袍公服闯进学堂,丑陋而狰狞的样子吓得先生跳窗而逃,吓得学生们“哭的哭,叫的叫,跑的跑,躲的躲.”我们与其将这理解为制造恐怖,还不如理解为制造笑料.李逵在狄家庄冒充法师捉鬼,骗了许多酒肉狂吃暴饮,然后闯进房里一斧砍杀了一对装神弄鬼的偷情者,并在死尸上乱剁一阵,笑道:“眼见这两个不得活了.”说书艺人在此处的主要意图还是制造笑料,只是有些过头了.即使是一些重大严肃事件的描写也仍然带有娱乐消遣的意味.如打破祝家庄后李逵闯入扈家庄,赶走扈成,杀尽扈三娘一家老小,回来后遭到宋江训斥,李逵叫道:“你便忘记了,我须不忘记!那厮前日教那个鸟婆娘赶着哥哥要杀,你今却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亲,便又思量阿舅、丈人.”此类取悦听众的笑料的穿插大大降低了事件的严肃性和真实性,换句话说,作品中许多暴力行为和暴力场景的描写带有明显的虚构和夸饰成分,其目的是为了迎合都市听众和读者的审美心理,而大多数听众和读者也只是把这看作演戏,消遣,好玩,未必真的拿它当一回事,所以,我们不必过于认真计较.诚然,这种为取悦观众而渲染暴力的做法,影响是消极的,今天的人们无疑应该抛弃这种不良倾向.
追求娱乐消闲的都市文化对《水浒传》的确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我不赞同夏志清、陈洪、孙勇进等先生的看法———小说肯定暴力而否定文明.尽管《水浒》的作者是由不同时期的艺人、文人组成,思想倾向比较复杂,但基本态度是一致的,即反对乱杀无辜,反对残害良民.比如宋江计赚秦明入伙和李逵劈杀小衙内两个事件,这两件事确实表现了江湖黑道的恶习:为达到目的而不惜乱杀无辜.然而,作者显然是不赞成这种歹毒的做法的,他写秦明“怒气于心”,“说道:‘你们弟兄虽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个.’”又让朱仝说道:“是则是你们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个!”这里无疑包含着对好汉集团乱杀无辜的暴力行为的批评.而对残害百姓的行为作者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第40回写江州劫法场,无人约束的李逵“不问官军百姓”,“排头儿砍将去”.作者让晁盖大声喊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第66回写梁山人马攻打大名府,虽然事前做过周密的安排,遍贴布告,晓谕城中居民不要随意外出,但在攻城之日却又未采取得力措施保护城中居民,导致一片混乱.作者写蔡福对柴进说:“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残害”.可是,“比及柴进寻着吴用,急传下号令去,休教杀害良民时,城中将及伤损一半.”作者不袒护梁山英雄,对他们在军事行动中造成贫民百姓的伤亡深表遗憾和不满.这些情节充分表现了作者爱护百姓、反对非正义的暴力行为的鲜明立场,怎么能说《水浒传》没有肯定文明?怎么能说“中国小说在对待正义的态度上含糊不清、对地道的暴力像孩子似的津津乐道”?[1](P109~110)
至于作者称赞梁山英雄平毁祝家庄和曾头市,能不能说小说肯定了“暴虐和贪婪”呢?我以为不能.平毁祝家庄和曾头市固然算不上真正的吊民伐罪之举,但祝家庄和曾头市站在官府黑暗势力一边,将梁山好汉集团视为反贼,发誓要“扫荡梁山清水泊”,活捉义军首领,赶尽杀绝,打掉这样的地主武装,谈不上暴虐蛮横.同时,梁山人马日益壮大,需要大量物资给养,寻找富有的地主庄园作为补给线,也说不上贪婪.
水浒世界匪气十足,但那是黑暗专制社会的造就;梁山英雄杀人放火,但决非杀人放火的恐怖匪徒所可同日而语;《水浒》作者渲染暴力场景,但并未葬送文明.